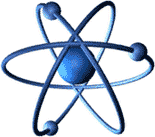Barb的不老歌
Jump to navigation
02 May
连环套
这两天没事老在后花园挖旧贴,眼睛吃冰淇淋。
并发现了许多转贴的林弈华文章——忽然想,我是什么时候知道林弈华这个人的?是水木乔纳森的一篇旧文章《拒绝影印的孤本》给我揭出端倪——原来是在迈克的书里,他写了个《到处睡的男人》,那就是林弈华。而林弈华又给达明一派写歌词,其中几句出名的,包括《命贱》“错对不隐,爱恶不侵,任末期盛世闹市光临;尺寸不甘,进退不堪,命贱无理,渐勇敢……”而与之同为达明写词曲的,又有何秀萍、周耀辉、林夕,梁基爵、亚里安、蔡德才……等等,后几人又组成音乐剧场“人山人海”……人山人海之前,达明一派以惘惘的电子乐重塑顽石绛珠的故事,那首《石头记》,是迈克为了前卫剧团进念二十四面体的同名舞台剧所作的——想当初,未发迹的杜可风正在为二十四面体及兰陵剧场掌镜。——毫无疑问,这是个小圈子,大家互相吹捧,一块儿努力,齐齐扬名,为的是在不那么商业的根基上,赢到更多注目。
像一个连锁反应,我对好多人的知与不知都是这么顺藤摸瓜来的。
——前天买了本《张爱玲文集补遗》,最爱读里面的信,给胡适、苏伟贞、朱西宁、夏志清等人的,见其真挚。其中给夏志清的最多,语气最熟。刚好半个月前,读林以亮的《文思录》,他洋洋洒洒数千言,一派赤诚地描述自己这位老友夏志清,他的朴素、博学与勤奋,以及北大耶鲁求学之路中一贯坚持的独立思考。里面特地引了一段夏的话,原文照抄:
“今天元旦,有位主编从台北打电话同我拜年,同时不忘催稿。拿出旧稿重读一遍,觉得这次圣诞假期,更不如往年,更没有时间作研究、写文章。自珍即要六岁了,比起两年前,并没有多少进步。这几天她日里睡,晚上起来,喂饱后,就要我驮她,一次一次驮着下楼梯到楼门廊空地去玩。她骑在我肩上,非常开心,只苦了我,多少该做的事,永远推动不了。驮她时当然不能戴眼镜。昨夜大除夕,美国人守岁,少不了喝酒。有人喝醉了,在靠近大门前吐了一地,我看不清楚,滑了一交,亏得小孩未受惊吓。二人摔交,我左掌最先着地,承受了二人的重量,疼痛不堪。亏得骨头未断,否则大除夕还得去医院照X光,上石膏,更不是味道。我用功读书,数十年如一日,想不到五、六年来,为了小孩,工作效率愈来愈差,抚摩着微肿的左掌,更增添了岁除的哀伤。”(自珍是夏的女儿,自幼身体不健全,到了晚上,脑波活动强于白日,非得父母轮流陪伴。)
——看了这段,我突然理解了为何张独与夏交厚。说到这儿有点跑题了,本来是想说,我何以知道去买林以亮的书呢?
原来林以亮又名宋淇。还是我初中时候,因为听了春节晚会上的《乡愁四韵》,于是买了本余光中的书《鬼雨》,除了《听听那冷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之类的题目外记住的不多,但记得余提到的几个好朋友思果和宋淇……反正都是这么丝丝蔓蔓的。余光中还提到思果参与过电影剧本创作,其中有功夫片《大醉侠》——这个《大醉侠》我小学就看过,这时印象加深,再若干年后,我知道它的演员有岳华,导演是胡金铨,是他导演了我非常喜欢的一出戏《龙门客栈》。
还有小时候读三毛的书,有篇《云在青山月在天》,谈到“三三们”,说“其实叫三三就像没在叫谁,是不习惯叫什么整体的,我只认人的名字,一张一张脸分别在眼前掠过,不然想一个群体便没什么意思了。”——一直对这个三三没有具体概念,直到看到《悲情城市》,编剧叫作朱天文,她可不就是那起三三文学社的人,又恰是张爱玲那朋友、翻译家朱西宁的女儿(阿城后来说朱文肖张,一样处处枝缠叶绕,浓得化不开,原来背后有这么个渊源)。
后来自己去看《花忆前身》,朱天文自己写《一杯看剑气》给三毛,适时荷西刚死,三毛未殁。朱天文说了句虬髯客最后对李靖说的话:“此后十年,当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与李郎可沥酒东南相贺。”十年生死,茫然若梦,她与三毛并无机会相贺再见——这早晚再回头看三毛,她当初是这么说的:“天文说三毛于三三有若大观园中的妙玉,初听她那么说,倒没想到妙玉的茶杯是只分给谁用的,也没想她是不是槛外人,只是一下便跳接到妙玉的结局是被强盗掳去不知所终的——粗暴而残忍的下场,这倒是像我呢。”
再有,就是西西。第一回看她,是白石桥旧书市贱价买的三本台港女作家作品集,有廖辉英的《油麻菜籽》、施叔青的《愫细怨》、刘以鬯改写白蛇传的《蛇》、师太的《独身女人》……还有西西的《我这样一个女子》,讲一个女孩去赴男朋友的约会,她知道男的将要向她求婚,因此这将是她最后一个约会了——她是个殡仪馆的化妆师,没有男人能忍受那双惯于抚弄死尸面庞的手与之肌肤相亲……又过了好一阵,才看到亦舒大力吹捧自己的好友西西,原来此西西就是彼西西。紧接着,林以亮又花了老长的篇幅,描述西西的《哨鹿》(写乾隆秋狩的一段故事,仿音乐节奏)——这几人又圈成一个圆。
最新近的例子是李欧梵与太太李玉莹合著的《过平常日子》——这本书本意是仿《浮生六记》,实际写的呢,骑着什么马也追不上沈三白的水平,李写的比他太太更还不如——又跑题了,就是在这本书里,李欧梵说起老同学白先勇,原来两人是当年台大外文系的同学。
哦,李欧梵原来已经这么老了?——我还记得,是年少时的三毛,读了《玉卿嫂》,又读了《谪仙记》,却怕这个作者,怕一个自小便眼熟的人,“看到这人迎面来了,一转身,跑几步,便藏进了大水泥筒里去。”三毛自己说:“三十年前与白先勇结缘,三十年后的今天,多少沧海桑田都成了过去,回想起来,怎么就只那一树盛开的芙蓉花,明亮亮的开在一个七岁小孩子的眼前。”如今又是几年呢?三毛去世也有十年了。
本来是想写怎么通过一个作者又得知另一个作者的,得出的结论不外乎物以类聚这种简单的道理,结果还没写完,拉拉杂杂先扯起来了,罢了,就是这么老起来的。
posted at 13:35:00 on 05/02/03
by
barb -
Category:
Life
Comments
Add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