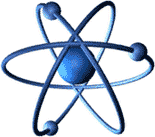Jump to navigation
Barb的不老歌
17 April
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昨天去看望奶奶,看到弟弟的新版《罗丹艺术论》,忍不住抽出来看看。这本书我小的时候,妈妈一直催着我看,但我根本看不进去,因为翻译过来太晦涩了,哪儿比得上当时正热衷的《三个火枪手》好看!而且,雕塑一旦化为静止的照片,就立刻“死”掉了。虽然雕像自己不会动,但每一根线条都是活的,照片,让人该看哪一个侧面好?于是,这回我翻看书里的彩色照片时,使劲地“想”着从里面尽量地捕捉雕塑本身的生气。
迈克曾经纳闷,罗丹那么多惊心动魄的男体,而他一辈子却被“证明”是异性恋的。那我真要怀疑,偶像难道没有去看罗丹的速写?成篇累牍的裸女,有的泛着情欲的光。他分明是喜欢女人的。从照片上看,“皮克梅林和加莱塔”,和“爱神与波塞克”两座雕塑都洁白莹润,其中的女体可以用“娇嫩”形容,那沉默中包含千言万语的两个姿势,可以用苏伟贞的一篇小说名形容——“世间女子”。
在“女性美”一章中,记录者葛塞尔问罗丹,是否认为古代的美远胜于现代的美,现在的女性远不能和菲狄亚斯的模特儿相比,罗丹说,绝不是这样!“那时的艺术家有看得见美的眼睛,而今日的艺术家都是瞎子,所有的区别就在这里。希腊女子是美的,但她们的美,大都是存在于表现她们的雕塑家的思想中。”
即便如此,罗丹最“惊心动魄”的作品仍然是男子。别的雕塑,不看见真物,很难讲。可是那座“浪子”,即使是拍成照片、印在纸上,那人的精神、气质仍然呼之欲出。那短腰身、长手臂分明是变形了的,可是块块缕缕的肌肉,却累加甚至“乘”出一种“真实”,不管这个人物离现实多么远,却是“逼真”的。
罗丹说,他做了夸张处理,以显示哀痛和祈祷的热诚。葛塞尔说,瞧,大师,你可是改变了自然。罗丹说,“没有的事!我没有改变自然。或者不如这样说,即使我改变了,那在当时也不是有意的。感情,影响我的视觉的感情,向我指出的自然,是和我抄下来的自然一个样的……如果那时我有意要改变所见的东西,要做得更美些,那恐怕反倒不能做出任何美好的东西来。”
当年错过了这本书,真是遗憾。
15 April
继续旁观
今天看了“且说说我自己”的后半拉和一篇“中国人为什么画油画” ,再胡扯两句。
1. 艺术、艺术家
陈丹青说了一段对于艺术与艺术家的迷惘,值得想想。他说艺术史上,分明都是艺术家,没有艺术家何来艺术;但是在批量刷出的行货里,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或者可以叫这些人工匠,但中国古建筑、壁画里没有留下名字的工匠,统统不算艺术家?
他说道,“我长久迷惘于委拉斯开兹的魅力。在他的画中,只见艺术,不见艺术家。”——也可能是印刷与原作之间沟壑太巨,我还没有领教委拉斯开兹的魅力,因此对他的画只有一个极其简单的感受:那满眼的艺术都是他自己——不动声色也是一种声色,他依然是旁观者。
2. 心灵、隐私
被人在众人面前问道,你的初恋是怎么样的,恐怕除了过度水仙花儿的,谁都不乐意,何况这个人是陈丹青。陈丹青真是一个对艺术认真的人,过于热爱一个东西了就会导致极度的严肃,再加上我怀疑他性格是颇有洁癖的,这种严肃就赶走了一切、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幽默感。但是起比很多庸俗的幽默感,这种严肃挺可贵。
另外就是,即便有这种极度的严肃,陈丹青还是一个心软的人,推却不了人家热情的邀稿,推却不了讲座,无可奈何地“三陪”,我一想到,陈丹青的家庭生活照刊登在ELLE上,就想笑。难道Cosmo“热情”地邀请他,他也去?画家在时尚圈子格外是一种流行人物,他的严肃和这流行真是格格不入。
别人传说他在伦勃朗面前流过泪,他说那是胡说,却坦率地认为有时流泪简直是“欢欣的经验”。他说罗兰巴特在念亡母的《明室》中讲的始终是母亲的形象和照片,但在书里的照片中既没有母亲也没有他自己,并说:“我要发表心灵,而不公开隐私。”这话说得真好,可是仔细推敲,心灵和隐私中间有一条模糊的界限。
我猜陈丹青写文章,比他讲话更坦率,因为够时间思考和回顾,不用怕瞻前顾不了后,口无遮拦得罪人。而他对于流行和名气的隐忍,在生活上,倒是更好地保全了他自己。
今早在报纸上看到被追认的物理天才束星北的故事,他被称为“科学界的陈寅恪”,李政道吴健雄都曾受他启蒙。他和王淦昌是好友,命运却截然不同,他被迫害、写检讨,七老八十才恢复名誉,然而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研究也做不动了,死了捐了遗体,还被遗忘在太平间里,被发现时已腐败,草草掩埋。别人分析他的遭际因何如此之惨时,指出重要的一点是他恃才傲物,不把任何庸才放在眼内,极度坚持真理,绝不给任何人面子。搁现在,基本上会被说成“缺乏EQ”,即便时代再怎么进步,这样的脾气仍然是祸非福,被迫害不至于,但也很难成名成家,一不小心成名成家,估计牵绊于人、事,既难保持心灵的纯粹,也难保持隐私的清静。
傅雷似乎也是类似脾气,虽然我实在喜欢不起来他那“家书”的口气,然而从《艺术哲学》的注里,还是看得出他在艺术上的才华,甚至有点惊艳。这一位也是对艺术痴情到了高度严肃地步的人,所以赴死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我们普通人的惋惜其实没太大必要。
3. 为什么
学油画的中国人,好象好多都羞于回答,自己为什么画油画。画画的人我认识的不多,除了好友的老公(还没见过面),我的堂弟,就是小船了,他们学的都是油画。好友和其先生是藏族,对于到底学汉族的水墨画还是学西洋的油画,好象没什么难于选择的。堂弟呢,自己虽然学西洋画,可是他父亲,我叔叔,是一个书法家,中国艺术固执的拥护者,在家里是中央集权,绝对比弟弟强势。小船呢,根本弃专业于不顾,死心塌地地喜欢国画。
陈丹青说,曾经被人凌厉地质问,“中国人为什么画油画?”通篇都是问号,为什么,中国女人也早早学会了三角裤露大腿的西洋风情,何时起,中国人忽然踮起脚尖跳芭蕾,揸开十指弹钢琴,正襟危坐听交响乐……咖啡香槟威士忌地往嘴里灌?问到最后,问得自己没了回答,弄得委屈而执拗地希望,能够理直气壮高回一句:我不知道!
为什么,中国人“不应该”学油画?
我支持Jun的宿命论,人,降生在哪里,根本是偶然性。为什么降生在中国的,不能大拇指抠进调色盘,用刷子在布上涂抹?不过是个工具而已。当然中国人或任何第三世界国家这样受洋玩意儿的影响,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种种原因,任拣出一点都可以钻成一篇博士论文了,但姑且想得简单点,人如果能够在多样化的工具中进行随心所欲的选择就好了。
我到现在,受到的西洋画的震动远比中国画的大,那既不因为中国画不如西洋画,也不因为我不爱国,而只是单纯的对于这种载体的倾向性——对色彩和光影的敏感,那种层层叠叠的,即便是一个颜色也能看到不同层次的质感,太动人了。也许有一天我也懂得欣赏中国画了,如果往前能随时看到无穷的可能性,有多好。我想毕加索画中国画、石黑一雄写The Remains Of The Day也是一个道理。
可是画了几十年油画的人仍然有这种重负。这种自我约束和责任感当然是出于很好的意愿,可是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生活在渔樵耕读的世界,这种自我挣扎和压迫岂不过于痛苦,类似自虐?另外,我总觉得,也可能是美好但不切实际的希望,美好的东西自有其生命力,除了天灾人祸,难于彻底地湮灭。(为什么老有不是从业者或艺术家的人不断地担心,“国粹”的消逝?)而这天灾人祸,某种程度上,是人力难于避免的。
不知为什么,即使我是西洋画的爱好者,有时却不免隐隐觉得,某个年纪之后,我始终会再“发现”和爱上中国画,这种感觉在看八大的画时最强烈。看,这才是民族性作祟,赶也赶不走的。
14 April
旁观
按着蚕给的地址,偷偷读了点《退步集》里第一篇“且说说我自己”,赶在老板杀回马枪之前,记了点鸡零狗碎的感想。
1. 自己
陈丹青说向来怕进门坐下就滔滔不绝谈自己的人,又说只要坐下文章,即便写的是天边月地上草,无一不是谈自己,但见到文章里出现太多“我”字就反感——其实这两者又有什么分别,我自己有时也小心地避免“我我我”,惟恐予人太主观的印象,但是反而觉得虚伪。
我的偶像迈克,洋洋洒洒写了大堆文章,篇篇都是在自家门口打转,我好象偏偏被这种“惟我独尊”吸引——说白了是满足了偷窥欲,作者通过这种“暴露”,达成了完满的自恋。迈克也不讳言,说自恋是生命中的甜品,没有它固无不可,但有了它生命变得格外多姿多彩——肯下力气欣赏他人和世界的人,多半喜欢以己度人,先是喜欢了自己才爱上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基本上自恋是自爱微妙的前奏。
比较可怕的是,有的艺人做宣传,不说“我”怎样怎样,而是象称呼别人一样叫着自己的大号,比如说“郭富城一定会blablabla……”(当然,我喜欢郭富城),这是Cathayan爱嘲讽的怪现象之一。
2. 自恋
看陈丹青未出国前的西藏画,并没感觉他是个如此细腻(到了敏感的地步)的人。比如他说开画展前看着自己早看惯看熟的百多幅旧画,“有点亲腻,有点烦”,“每当这样的打点布置自己的展览,我多少像是置身事外,并茫然惊异于自己的冷漠”,这种对于自己漠然态度的突然发现,他自己归结为“一种难以弃绝的自顾与依恋”,我顺手就给简化成了“自恋”。可是不自恋,活着干啥。
我听过的歌里,最自恋的就是张国荣那首《我》了,“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可见林夕多么自恋,惟其自恋,才把自己边边角角的心情都收集起来,写了那么成百上千的歌词——虽然大多数看着都差不多,不过总有几首妙到毫巅的,打动了我。
3. 作家和作者
陈丹青的文章有和阿城类似的气质,那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好,不过Cathayan都不喜欢。我估计是忒有点城市里文化人的“端着”——虽然他们并不想出风头,虽然他们保持着自认为的低调,可是总还是不经意地透露出一种“自己与他人不同”的区分来。当然每个人是独特的,意识到自己的独特那也是成熟者的自信,没什么不好。可是他们给人的感受却有点文人气的捏弄,而和阿城做过访谈的姜文也是大喇喇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但是这个人的与众不同Cathayan能接受。首先可能是他的语言是电影,电影这东西作为一个工具或“武器”可能更中性,镜头长也好短也罢,晃得厉害也好端得四平八稳也罢,总之随你自己的习惯和理解去看就好了,而文字呢,尤其是累积了几千年文字传统,已经被扭曲了又扭曲,影响了又影响的传情达意的方式实在已经不像电影语言那么原始而随心所欲了,所以端着是容易的,不端着是真厉害,可是能做到“不端着”的又有几个?
Cathayan非常接受《冷山》作者那样的语言,这个作者好象从来不是作家,而是个农场(牧场?)主,写的文字大概本身就脱离了作家所受到的“敬业”的限制,因此易于翻译,翻译过来,字也很浅,就是很简单地讲故事,讲心情,观察……不得不承认,天分之外,有的表述方式确实受到了生活环境的熏陶,看惯大山和开阔的草场的人,整体气质和哪怕是受过良好训练并且有天分的写手还是有巨大差异。所以我感觉好的写作既不是力气活儿也不是脑力活儿,而是比谁运气好——恰好是天分、经历、环境的完美结合,或者说,是胸襟的比拼(胸襟如何,跟运气真是大有关系)。好象类似的话以前在书上看到过,但还是自己碰到了想一想,才有点儿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