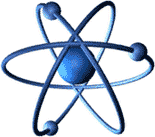Jump to navigation
Barb的不老歌
12 May
来日方长②
刚开始,我还带着轻蔑的态度去看《荒人手记》呢,以为这百无聊赖五光十色的人生不过发祥于台北方寸之地,偏居一隅的作者自造出来的假像,读着读着,十几天断续着读下去,竟读出欢喜来,这幻像大得像夜晚霓虹的幻彩,伸手抓不住,却是城市生活近在咫尺的真实的幻影。
“若再有一次机会我会说,新时代?当我们年轻,貌美,体健的时候,谁理新时代!没有前世,没有来世,只有衰老,然後死亡,这个事实。”哈!
情绪低落时必然看几个台港女作者的书,黄碧云,苏伟贞,朱天文……黄是迷乱而真开脱到了外界,世界广阔无涯里的小我;苏伟贞写起长篇来没逻辑,可是晦涩得渐渐你也就看得心静了;朱天文我一向并没有高看一眼,因为《荒人手记》改变态度。是时正好看白先勇异乡两篇,Danny Boy和Tea for Two,巧的是,一样说起那场大瘟疫,疫后大惊失色的孽子余勇,白先勇是温存圆融的叙述,始终有声有色电影般一幕一幕,凄凉也有大团圆的味道,《荒人手记》却像梦呓,自己对自己说,说完了天地皆不完满,伤痛太多,情极迷乱,一切不知背在谁身上,渐渐地托无可托,也就化成了荒凉,像一阵烟。真正的创伤原来不止痛而已。
也不是一个作家写流行,面膜时装明星佛经更引用法国女性小说若干,然而时代的复制本有新闻纸,连寻觅十二少的如花也要向报馆寻回仓促的约定,要小说家不如要复印机。在时代里活得滚烫,又站在时代之外冷看一眼,是小说家的机巧,更是本事。朱天文的本事大呢。
广场上集体欢庆,人山人海,站在人海里你笃定或恍然若梦?那果然是“没有身份认同的问题,上帝坐在天庭里,人间都和平了”?
“那样秩序的,数理的,巴哈的人间,李维史陀终其一生追寻的黄金结构,我心向往之,以为它也许只存在於人类集体的梦中。”不是在人类集体的梦中吗?《光荣与梦想》,所谓集体记忆,是一个又一个人狠敲两钉子,乐意记住的,镌刻入史书,而后翻阅,可惜此集体非彼集体,各有各集体,于是黄金结构终成一梦,还有人不信数理,还有人不爱巴赫呢。
很多人推荐福柯呢,他们说,福柯好福柯好,又仿照福柯写文章。《荒人手记》干脆把引起过作者沉思的典籍作者拉下水,一会儿是李维史陀《忧郁的热带》,一会儿是福柯《性史》,不光提及大名,引只言片语呢,干脆大段总结、简释,仿佛是边生活边思索的进程,边阐释又边质疑,还有幕后八卦,啊可知写小说是多好的交流方式,是自语及告之,向不可知的世界剖白,也许所有的疑惑都有陌生人应声,这儿又有了时代的影响——网络自四面八方聚拢人,同一癖好者如受制于向心力般,向同一目的靠拢再靠拢。《荒人手记》不是为这电子的时代,可它和这时代多么相适,多少私人感受在这世界得到大同。
是诀别呀,上帝之手碰触亚当,分离的一线。像多少婴儿脱离母体,像多少少年离开家庭,自混沌中来,又向混沌中,披荆斩棘,开辟自己的去路去了。用笔写音乐,写画,用画透露情感,音乐流着诗,又比画还真切……五感相通,缠夹着进小说,小说最好,是因为文字最简单质朴,掀纸能读,大不了上IE、Mozzila,瞬间把你带到西斯廷,地中海,地角或天涯。
半夜,阿尧越洋打给他的电话,说道《欲望号街车》里白兰芝的传世台词“我一直依赖陌生人的慈悲……”(我们内地的译法一般是,“不管你们是谁,我总是依赖陌生人的好心”)朱天文向田纳西威廉斯致礼又致礼,我纳闷她研究了他多少,又八卦又崇敬地。我但愿自己有这样的热情,上天入地花时间心血这么研究一个人。
10 May
来日方长①
我还很笃定地认为,《荒人手记》在我那几本朱天文的书里一定有呢,前几天想看,翻来翻去发现没有,懊恼了一分钟,换成看《花忆前身》。然而散文和小说大不同,我看真故事老是有股烦闷,觉得那股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又把人和现实压逼得很近很近。文字是为另一个时空,才是好的。
今天扒来扒去,好不容易找到这篇小说,就着显示器上密密麻麻的小字儿,就看起来。看到“他”和阿尧出游,电光石火仿如初次相见,突然另一个自己走出来,两个男人皆又惊又惧,朱天文写道,“我看到不该看到的事实,迅疾掩住,已经迟了。”这句写得好,则为他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错付终身。前几天看了几集Queers As Folks,这个电视剧堂皇得很呢,也遮掩,但是展示的是欲遮无从的另一个世界,本来是雄性的动物们的天理伦常,偏夹多一点“是为人”的思虑,思多虑多,去日苦多。我就明白朱天文要写同性恋故事的原因了。
“我擦去不愿承认的真相,重新书写文本,於是我也真的忘了十分瀑布的实情。”行行重行行,记忆是可擦洗的呢?
两个男人,在一人大限将至之期,一起生生掀出记忆,背诵费里尼,八又二分之一,这个情节也只有在同性故事里我才能相信,因为他们具文艺气质者众。又说起小津,和阿尧的妈妈,在日本的房子,静中有动,动仍是静的生活,就在小说里入了小津的戏。到底是编剧,念念不忘电影。网上有消息,朱天文说,“写了《荒人手记》,我终于可以说:啊!和张爱玲平了。”别人一直拿她比张爱玲的,可是看到费里尼和小津一段,我是觉得还没有平,电影是现代人挥之不去的背景,恶霸霸地侵入记忆,遇见什么难能可贵处,就手儿拿电影来急就章,张爱玲不写哪个导演哪出戏,一段段故事自己就是电影。
阿尧一死,他踽踽独行,二人交叠的记忆随之而逝,我最信服的是,“无人共知,共享的记忆,有何意义,视同湮灭。”和前几天看的关于记忆的电影不谋而合,疯狂记录和寻找的,不是对方的记忆,而是自己曾经存在过的证明。
阿尧死之前,是生猛的同志运动家,他的回忆,百分百朱天文句式,“八七年华盛顿爱滋祭葬。八八年,曼彻斯特终止第二十八条。八九年,丹麦准许同性恋合法婚姻除了不能领养。九零年,kissing in,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如同那年看《世纪末的华丽》,时装界疾风一年一个方向,八九年雪纺亮片绸皱纱,九零年海滨浅色调,春风一度,还是这个春风,草却换了一茬又一茬。朱天文是时代的才女,手起笔落,喀嚓喀嚓映下时代的,比张爱玲的年月快了不知多少倍的步伐。
又说起,麒麟的广告。金婆婆银婆婆百岁老人。台湾人受日本流行文化“毒害”甚深,于是谈及小泉今日子言下甚哀。《世纪末的华丽》里,华伦天奴加里亚诺间,一定夹杂川久保玲MEN’S NONNO,就是这些记忆把台湾文学里的这个时空搁置在那儿,不中不日不洋,亦中亦日亦洋,难怪心慌意乱。八十年代的流行歌儿曾经说,没有人心疼你,只有自己心疼自己,这可不是外人难透彻理解的境地,自己心疼自己,香港的亦舒也一样。迈克更不用说了,心疼之余,有赌气的性质。
“当同辈的我们之中,越来越多人参禅习佛,信仰新时代,鼓吹整体健康,要从形而上的心念来统合情绪和肉体。当仙奴跟唐葫芦两人津津乐道前世追溯疗法,催眠疗法,再生,拙火,气提,夏克提,真气,自性,秘教密语的把我排除在旁,似乎他们握有进入来世的护照很可怜我却没有。我妒恼起来,不为没有护照,天啊那个地方我是根本不要去的,而是他们尽讲一些我不知道的专有名词,太没礼貌了,有失待客之道。我不悦说,新时代,何不承认它也只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一种慰藉罢了。”
这段我拍巴掌赞同,今年某月某日在某城,一返自加国二婚经理火锅桌上理论继子大谈禅宗,我们北京去的土人们由上到下面面相觑,后来发现此人是最不干活儿的——岂止慰藉,一不小心可以蒙人的。《荒人手记》本来没什么故事,起、承、转、折是潮流的身影,火山泥、海底灰,金橘茶到密宗,福柯,性史,什么风靡写什么,流行留下暗疮印儿。不比盖茨比的时代,爵士乐,白房子,已足够衣香鬓影的一生,熬过这个世纪末的人都遭潮流的劲风吹过,分不清东西南北,再怎么捕风捉影,也只留下满怀错愕一手空。
如此放浪形骸呢,难怪朱天文自己吁气,与张爱玲平齐,先是放笔不掩饰的勇气追齐了张爱玲奇装异服的胆量。田纳西威廉斯,色情乌托邦,麦克杰克逊塌陷的鼻子和怪癖,本来当八卦看也行,可是一则又一则,爆裂出来又丑陋又淫靡难于自控的动物性,作者说,“因为它们无法扩大,衍生,在愈趋细致,优柔,色授魂予的哀愁凝结里,绝种了。”既非褒义,也不是认同,借一个同性恋男子的口,说到那个重点,是自由至难以自控,自由的边界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