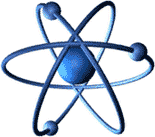Jump to navigation
Barb的不老歌
18 February
凉风有信,秋月无边
“小生缪姓莲仙字,为忆多情妓女麦氏秋娟……”这段粤曲“客途秋恨”,一想起来便想起如花——偏偏不是十二少,“客途秋恨”是借良人的口说出一段妓女多情的故事,也更显出了嫖客的薄幸——明明知道她的好,却又偏偏把伊抛。
李碧华文字上纠缠多年,写来写去也还是一个情字,要说看破,《胭脂扣》的尾声上,永定在街头听到卡门序曲——“什么叫情?什么叫意?还不是大家自己骗自己。什么叫痴?什么叫迷?简直是男的女的在做戏……你要是爱上了我,你就自己找晦气,我要是爱上了你,你就死在我手里!”——看透了还是要爱要恨要纠缠,真是女子命定的荼毒。
李碧华所有的书,《胭脂扣》最薄,却最好,她的书改编成电影的,个人还是觉得《胭脂扣》最好看——要说为什么女人容易被关锦鹏打动,皆因他是夹缝人,尽悉男女心事,才情高,心思又比女人还细。他选演员,每个都恰如其分,梅艳芳的如花,陈冲的王娇蕊,叶玉卿的孟烟鹂,张曼玉的阮玲玉。这一场,如花胆怯嗫嚅地出来了,向永定:“先生,我想登一段广告——”
永定后来问她,你那十二少,是怎样的人?“十二少——他是南北行三间中药海味铺的少东。眉目英挺,细致温文……”待永定细问,她又卖个关子,永定心道:“女人便是这样,你推拒,她进逼,到你有了相当兴趣,她便吊起来卖。”——一直觉得李碧华有股粗粗拉拉的豪气,这一笔写出塘西生涯的无奈——大家都是人,妓女却只能笑着脸儿作人,天下这么大,遇上个把人模狗样平头整脸的就拼尽心思用尽手段,“这只是生计……我晓得以白牡丹或银毫香片款客。我百饮不醉。我对什么男人讲什么样的话。但不过是伎俩。”——如花那时,不过二十一二,看的戏是《背解红罗》《牡丹亭》《陈世美》,纵然是见过世面的红牌阿姑,怎敌得过十二少的花巧,“一夕执寨厅,十二少送了如花一个生花扎作的对联花牌,联云: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
我要是永定,也不屑,“哦,在石塘嘴,倚红楼,蒙一位花运正红、颠倒众生的名妓痴心永许,生死相缠,所以他得以‘振邦’?嘿嘿。……不过是一个嫖客!”——可是,在电影里看见十二少陈振邦——张国荣扮了戏装出场,也觉得英挺——可见李碧华早就知道张国荣是什么样人,十二少还是个铺陈,后来才度身定造《霸王别姬》。吸鸦片的颓靡,张国荣的表情和《春光乍泻》如出一辙,糜烂中欲仙欲死——都是抗拒不了欲望的人,贴了乔纳森一句话“沉溺,不如沉溺到底”——在我看,其实未必想沉溺,只是陷进去拔不出来,只好给自己一个理由(什么道路,都自备哲学一套)——而容易“沉”的人,其实泰半敏感,而茫茫不知所终。
“廿四岁。才这么年青。往前瞧,一片锦绣。十二少对着这公共的镜屏,背后人声鼎沸,喧嚣纷纭,一切都淡出了。他一壁落妆,抹去脂粉,细看一张憔悴的不成人样的脸,自己都认不出来,那曾经一度的风华。”——这张脸,不用看片子,我认得是张国荣的脸。
凌楚娟当然嫉妒——如花是那么美的一个女鬼,她让我想起《香雪海》的叮当——叮当也姓凌,聪明巴辣,其实也是心软的(不管城里乡下,这种女性都多,让人喜欢)。帮如花寻找十二少是那么有趣的事(多好啊,看一段悲欢离合,感同身受,是因为不用身受,还可大发感慨),阿楚也分一杯羹。——我很服李碧华,一本书做那么多调查,得翻多少旧报纸。“哦,《天游报》。你怎会得知什么是《天游报》?告诉你,这是广州出版,专门评议陈塘、东堤,以及香港石塘咀、油麻地阿姑的报纸,等于今日的《征友报》,不过,文笔要好得多,你瞧,都是四六文。唉,你又不知道什么是四六文。……”
再翻一页,心惊肉跳——隐隐有的预感变真——这不只是永定的感觉吧,那两行标题是:“名妓痴缠,一顿烟霞永诀;阔少梦醒,安眠药散偷生。”如果《胭脂扣》到这里结束,也就是一个平凡的故事。最后一场,十二少投生为一段新闻:“陈振邦,七十六岁,被控于元朗马田村一石屋内吸食鸦片烟,被告认罪,法官念其年迈贫困,判罚款五十元。”——振邦,兴国,栋梁,每个父母起名字的时候,都是希望那粉嫩小儿日后造福天下的吧——不料他不但没有振邦,反而连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或者,根本没有爱过?——小时候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心里还叫痛快——现在不知有何可快。
“这便是人生:即便使出浑身解数,结果也由天定。有些人还未下台,已经累垮了;有些人巴望闭幕,无端拥有过分的余地;
这便是爱情:大概一千万人之中,才有一双梁祝,才可以化蝶。其他的只化为蛾、蟑螂、蚊蚋、苍蝇、金龟子……就是化不成蝶。并无想象中之美丽。”
——这样灰败的人生,是李碧华、亦舒的擅场。我心里没什么可黯然的,——却想起萧峰。
17 February
胭脂如蓝
看黄碧云的小说,只觉闷到极点,仍是不得不看,不得不痛的。
《爱在纽约》这个名字让人想起罗川真里茂的漫画《纽约纽约》,然而《纽约纽约》是现实里生造的浪漫故事,容你有片刻的感动,却是没有说服力的。《爱在纽约》,像黄碧云的《盛世恋》般,似是另一个与我们平行的世界里,有一把隔世的嗓音在叙述。只是感动吗?或许远比那更深切而痛楚,像宋克明在许之行跟前跪下,膝下紧紧压着一地的玻璃碎片。
之行说,你跪下的时候,还没有起来,你已经不爱我了。
——其实叶细细、陈玉与许之行三个女子,竟是谁也不可爱的,身上都有看不见的岁月啮痕,然而纠集三个女子,竟使文中的女人浮凸而现,像幽灵,像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克明周游于三个女人的身体,最终还是深深地跪下去,这一跪,不只是对着眼前的之行。
怀明是旁观这一切的弟弟,末了,他轻轻地抱着克明,“在人的自私而软弱的亲近里,寻求一点卑微的安慰。”他爱的是陈玉么,又再再记着细细对克明纠缠如蛇,还有之行,宽宽的有无限承担的肩膀,他便在这迷惑里,在克明的故事里成长起来,我有时觉得,他爱的,是兄长克明呢。
细细死了,克明经过之行与陈玉两位“妻子”,然不过是日复一日的争吵,再悄悄耳语,说爱(爱不过一字耳,腹稿都不用打就说了,风一吹就没),之行走了,只剩下故事里最没有性格形状的陈玉,说一句:“是我错了,错在甚么地方,我却不晓得。”克明说:“你要怎样才相信我爱你呢?”此时他对面空中难道没有细细与之行的影子么?这句竟是他欠细细的前生那么多眼泪。他说,“难道要我从这里跳下去,你才相信吗?”,“砰”的一声,他就跳下去了,如此轻而易举。他错了,只道舍身成爱,岂知爱字当头,身体不能为明证。
原该知道故事该是这么个结局,不然还怎么办呢,乱世般的纽约,凝滞了几个飘零男女家国岁月的半生,什么也没了,只余一丝儿爱情,然而眼前迷茫,伸手也不能抓住。
“原来细细秀丽如狐,笑声亮如一城的细钻;之行聪明剔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摸得很清楚;陈玉脸容时常都很静,克明满心欢喜。”……
觉得黄碧云讲故事的口吻正如她笔下句子,心如止水,不动如山,而山水又无限柳暗花明,中间透着,是她固执不肯放手的,“如蓝的胭脂”。而蓝,是个忧郁的颜色呢。
11 February
既见良人,云胡不喜
既见良人,云胡不喜,这是另一个论坛的朋友除夕晚上发给我的贺年短信,本是贺我和家猪得以在广州团聚,我却想起,他之前提到,在旅途中看完了《放色海外——杜可风非中国电影笔记》。那时他说:“十分郁闷,摄影大师的文字如此之好,还让不让人活了。”
好,这一下,心中关于杜可风的想法瞬间汹涌,而这书,他亦送了我一本,托人迢迢地从厦门带到北京,那么就写下来当谢过了他吧。
Christopher Doyle,这个名字,想必已和杜可风三个字一样掷地有声了。《放色海外》,正是写他去好莱坞拍片的点滴,他们重拍希区柯克的《惊魂记》(Pshcho),他作摄影师。其实最早看到这书,是几年前在还没搬家的雕刻时光,当时他的书有两本,另一本是拍王家卫电影时的笔记,有《重庆森林》等片子的现场照片,显然更诱人。可是两本翻过,浮光掠影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话,却在这本《放色海外》之中:
“对我来说,电影既是亲近,也是距离,好象是最熟悉的东西出现在梦中。电影是让我们在更好的光里,将每天耳濡目染的事看得更清楚、变得更有关连。电影,是让梦变成真。拍了三十部电影,一直在电影圈里往前走,我发现你不然就是在自己家后院拍,不然就到你最想去的远方。我们的电影游走到世界尽头,又回到自家方圆几公里内,那么近又那么远,the space of a kiss。”
The space of a kiss,没有一句话更能描述电影了。也许,只有看过《春光乍泄》,这一句于他的意义才更清晰。看《春光乍泄》,忽而黑白忽而彩色的节奏,摄影师在幕后么?片中隐约看到的都是他呢。都说《天使爱美丽》里的红与绿好,且不知在《春光乍泄》中,在探戈曲里,杜可风早已用镜头做了铺陈。都说电影里看得出导演对演员的感情,且看看《东邪西毒》里的张曼玉——杜可风是学中文出身,他笔下再好,仍不如一部摄影机的情生意动。
杜可风早说,他爱女人,“不管你相不相信上帝,我觉得看到一个美丽的东西都能扩大你对于生活的乐观态度,扩大你对生活的享受。我的生活里最美丽的是女人。”这句话,在《暗恋桃花源》,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早有了印证。且不说赖声川、关锦鹏这两个我最爱的导演,在杜可风镜头下的林青霞、叶玉卿都是极美,而这份秀美,竟是岁月无惊的,带着辽远之气。
顺带翻开《放色海外》,有我非常喜欢的一句,他说许美静(是他导演的片子《三条人》的女主角):跟张曼玉、舒淇一样,许美静也有一种我不能亵渎的纯洁。
回思自己用摄影机创造的空间,他曾说过,“有点象张曼玉在《阮玲玉》里面跳舞那个样子。我觉得从那场戏开始张曼玉才是个演员,之前是一个美女。”杜可风的这场惊变,可能始于王家卫,到最后水墨般漫洇开去,竟成自己的一片江山了。
在《甜蜜蜜》里,他演的英文教师“斋卤味”,教人“You go to the hell. I go to the hell. We go to the hell.”最后陪染了爱滋病的女友回她的家乡菲律宾,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了,脸上却一派平实。他,还有片中黎明姑姑对威廉荷顿的一生爱恋,都是在主角外,令这电影再也不能忘的。
回到最初,他出道时还曾为云门舞集和二十四面体摄影呢。也许用笔或键盘,用一些苍白的句子,并不能描绘一个隐身于电影,却如此多变的摄影师。就用他自己的话吧。
他说,拍电影就是“与生活做爱”。
他说,你不犯错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对。你最重要的是要有判断力,是要勇敢一点,能推翻掉你自己以前所肯定的东西。
他说,你要寻找适合你自己的一种方法,适合你自己的一种风格,适合你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适合你自己跟别人的来往方法。这些是绝对的。一个晚上做8小时的底片,一个礼拜以后,你会发现大概有百分之八十是狗屁。不过有一些,会通过去除掉的障碍留下来,而你内心的东西真的会呈现。
在《放色海外》的封底,他更是说:
“人们有一种错误的期待,以为一个吴宇森可以改变好莱坞,相信政府赞助可以培养出好电影,或是,相信任何一部杜可风拍的电影都是大师之作。
事情才没有那么简单。问问大卫普特南(David Puttnam)或任何一家电影公司老板,看看多少吴宇森的想法被电影公司的大头目左右,甚至大卫林区(David Lynch)和张艺谋有时都得眼睁睁地装傻。
我不怕老是丢脸,我喜欢到不同地方工作迎接挑战,但找我拍电影不会让你变成一个王家卫。我们都需要方法、空间和方向去拍出理想的电影。我不是一个人的军队,一部电影一定是由一群人一切共同完成的。”
看完了,或许你也和我一样,心想,这才叫胸襟呢。在这之前,一定得去看看他拍的电影,那里面藏着他的爱呢。每次看到那些熟悉的镜头,我心中的感觉可不正是这句,既见良人,云胡不喜。
09 February
谁不是、其去未知
又看一遍朱天文《风柜来的人》。
阿清回忆里的快乐也真实在——五爪苹果,姐姐那爪是弄到香黄的苹果肉都锈了,才用门牙一点点刮着吃掉——朱天文就是这点尖利,每半个句子都浓冽,刀削斧凿般劈下去劈下去,一丝儿怜悯不容——根本是个童话故事光明快乐的结尾是罢?惜乎只是阿清的一个梦,还不是歌里唱的,“微微风涌起旧梦,拾起一片回忆如叶落”那样绵美的旧梦。朱天文写东西总是这样有现场感——父亲给贫困之家带回苹果、绿豆糕后的欢腾,穿插的是后来父亲伤残(因被棒球打到太阳穴,又是一个戏剧化,令人压抑不住诧异,又不忍),阿青给他喂饭,喂得急呛了一口,母亲恨得骂这个变成混混的不肖子——阿清喂着时,是想起幼时父亲和他打蛇一场,那时本是个年富力强能挡风遮雨的父亲。
朱天文某次拿奖,被说是张爱玲,她不敢当——在我看过的同期作家的作品,下笔嘈嘈如疾雨的,朱天文是个异数。阿城说:“我对朱天文的微言在于,朱天文对她把握住的对感觉的感觉,有时手下太密了一些。比如她的《荒人手记》,有点象李贺写诗。诗也许可以,但长篇重结构,连梁架墙壁都卖得大价钱,挥霍了一些。不过话说回来,也只有朱天文才挥霍得起。天才常常是挥霍的。”——张爱玲也是——不算短寿,却觉得还没有把才华挥霍得尽,铺陈到底,天分太浓了。
“沙上平躺着两个人,空寂的海边再没有别人。黄昏一寸寸、一寸寸蚀掉海岸,最终一暗,太阳沉到水里,沙上起了风,细细清清的晚凉的风,叫人很累,很累的,想丢掉这一身臭重皮囊,让潮水把自己带走,走得远远……”少年初识愁滋味,而阿清未必明确认识这是愁肠——“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殷正洋的歌?的声音?),乡里少年哪有这细伶伶的肚肠,纵使相思也夹在了求生和适应新生活的夹缝——那是阿清、阿荣、郭仔一道入了高雄以后。
去高雄前这一幕,在我眼中不是两个人——是他们三个靠在沙滩边的矮墙,波浪一滚一滚,我记得自己中考前也是这一幕:既百无聊赖又满腹愁肠——我看的是胶片,侯孝贤那永远象是破败的画面,我太知道朱天文为什么能一直成侯导的“御用编剧”了,她特别擅长刻划年少的无奈(谁说少年不知愁),愈加显露成年的苍茫,本身已经是戏剧化的——回身一望,哪个人的成长不是一部冲突史?心事难与君说,当下已是,拔剑四顾心茫然。
到了城里,第一遭就受骗——说是看毛片,先收费,三个乡下少年懵懂付了钱,按指点上到七楼,按捺紧张与好奇,才发现是彻头彻尾的空楼架子,钢筋水泥窗户望出去,是城市无尽的霓虹灯光——这幕留在我印象里的是电影,活脱从书里蹦了出来,却只是一小段。
租房、做工、遇到小杏——小说、故事里,仿佛总有一个女人中途走出,成了那个男人的劫数——反之亦然。电影中的小杏,皮肤微黑,浓眉长睫,头发黑蓬蓬,时常穿着睡衣,一抬手腋毛露出来——满打满算的粗俗和活力,青春逼面而来,我要是阿清,也眼晕。小杏是非常坚强的女人(想到阿清的妈妈,着墨不多,然而多少女人就是这样过来的),有主见,只有黄锦和降得住她——这部戏里,锦和是庹宗华演的。庹宗华在我眼里地位特殊,不象张震那样野性十足又透着忧郁,易讨好,可庹宗华又不是全是个斯文人,有时候蓦地一眼,瞪得人心里一凉。书里倒没怎么写,电影里,一早知道他要抛弃小杏——各人有各人命定的遭遇。瘦瘦巴巴的阿清上去一比,简直神情猥琐,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然而谁说猥琐就不能有纯真初恋?和父亲打蛇的事,也只会说给小杏听。
“阿清喜欢这样的,这样走在夜市一溜灯火通明的街上,有时候小杏落单了,在摊子上买发夹别针劳什子,有时候又跟他脚边像只小猫咪。让他觉得这花花世界都是他的,而有一个人永远在那里看着他。”
终局,小杏自然是走了——世界这么啊,也只有自顾自活着。阿清大喊一气,也只就这么忘了吧,生活从此一把大浪扑过,掩埋所有。
“看得见远空中一叠两叠暗云,与沙滩上三个灰条条浮移的小人。潮岸不知伸向何方。他们亦将是,其去未知。”
附:袁琼琼《天文种种》一段:
而《风柜来的人》,虽然天文说是电影故事大纲,我却喜欢,又胜过电影。我对电影《风柜》情绪复杂,肯定那片子真的好,但是一点不喜欢,有天跟柯一正说那片子是:“人到处晃来晃去,什么事也不做,浪费生命。”柯一正说:“那片子要讲的就是无所事事和浪费生命啊。”
02 February
天文眼里照天心
过年本来想看几本漫画,电视上再看几出重播的旧片,和和美美过了——连《NANA》、《鬼外事件簿》都买好了,零食也备齐了,却还是忍不住,一下一下地跑去看朱天文,每次好好地放回去,下次又翻出来,看了又看,爱不释手。
朱天文写散文离她的生活甚近,离侯孝贤的电影却去得远了远了。薄薄的一本《花忆前身》,倒有许多写她妹妹天心。这一套文集,原也是为她们朱家三姊妹出的,朱天衣是哪一本忘了,朱天文与朱天心的分别是《悲情城市》、《炎夏之都》、《花忆前身》,和《江山入梦》、《方舟上的日子》、《古都》。
从前离朱天心甚远,记得深切的是《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结尾把“三三”们,把三毛齐豫这些朋友假作幼年的玩伴一一数清,像达明一派的《今天应该很高兴》:“伟业独自在美洲,很多新打算;玛莉现活在澳洲,天天温暖……永达共大杰唱诗,歌声多醉甜;秀丽伴着乐敏肩,温馨的脸……”这样地历数故人,完全不避嫌地,满满的一腔热血,却是岁月惊心。
天文说天心,“她是深情于现在这个世界的,声色犬马,她爱。”——风闻打折,天心跑去抢购内裤十五条,天衣、天文各五条
看过《E?T》,又挤到天文身边耳语:“你不要跟人讲,我觉得我很像斯皮尔伯格。”《E?T》里,那大而圆的月亮,飞车穿行,几万年的地球都被照亮了。朱天心的斯皮尔伯格不是这制造梦幻的家伙,却是那躲在大导演背后不安、羞怯、神经质的灵魂,怕乘电梯,仿如天心——如果出事,瞬息万变的构思不知道该交给谁。
看过《西游记》,她又要命地爱上了孙悟空。天文笔下,旁观她爱史,读荀子,说话与苏轼同调,又写一篇三万八千字的《时移事往》,皆因爱着一份肝胆相照。然而悟空之恋是段注定了然无望的爱情,天心也会叹:“唉,他是个猴子!”——此时不免想起日后《大话西游》,结尾那莽莽苍苍的音乐,卢冠廷一把苍凉的嗓子唱着《一生所爱》(“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漂泊白云外……”),那至尊宝笑道:“他好像一只狗哎。”
对原名《爱波》的《时移事往》,天文又说:
“爱波如果是时尚的弄潮儿,天心化身为叙述观点的男子,就是晴空旷日下湛蓝的大海。潮涨潮落,花开花谢,他那样包容、好意,尊重这个世界。他的柔和,又如菩萨低眉,重望扰扰红尘里生老病死。”
“爱波最是身在其中之人”,那么天心亦荡荡于这尘世中了。
她与她竟不似姐妹了,有时客气得还似生人。天心在等车的红砖道上发现了“全世界最好吃”的巧克力,硬要掰一块请天文,天文知道巧克力价贵,推脱半晌才接,坐在车里极慢地抿着,“当心太快吃完了她又会给一块。”天心也有些害羞似地只顾埋头品尝不出声。这极近极近有时反化作生疏,我便想及我的妹妹,也是如此呀,全为互相敬重及欣赏,有时反想得比生人还细,她护我时反倒像我姐姐。这番感同身受,是真真切切的。
天文便是一笔笔雕凿出这样一个天心,“深情在睫,孤意在眉”,仿若那明代女伶楚生,穿越几百年的时光又回来了。而她自己,有如临水照花,竟也在这几番低语中历历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