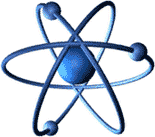终于买了陈丹青的《纽约琐记》,越看越兴奋。记得以前帮朋友买这本书时它还一度缺货,就是因为替朋友买多了,自己也想买(书是上下册塑料纸密封,所以买了也不能翻看)。第一个托我买书的是在拉萨的最好的朋友,她的丈夫边巴是位画家,当时将要去纽约办画展、作画,听说有这本书就等不及在拉萨找,急匆匆地托我买了寄去。陈丹青的一部分名气恰好也是因为毕业时画西藏大画。有一次看中央1台“美术星空”(这个节目挺好看,可惜总是白天放),陈丹青的师友回忆这段事,陈丹青从西藏回来、从箱子里取出画的样子仿佛历历在目。第二个托我买书的,是好友的表姐,曾在藏学研究中心翻译藏学资料(藏文译成英文),表姐比我的朋友长得更像藏族,但又很古典、美丽,长发天然卷曲,她因为不喜欢而盘成髻,偶尔披散下来,是要让人惊艳的。她在旧金山呆过一段时间,可能是异域的经历,又是一个喜欢古典气的艺术的人(她喜欢的片子,都是《钢琴课》那种类型)(陈丹青自己,活脱是古典长相),她一听我给表妹买了这书就立刻托我代买。
看陈丹青激动起来,是因为《纽约琐记》不是一本纯谈艺的书。看时突然觉得,很多对人、事的看法,真不能让搞文字的人来说——要让另有专业的人闲闲看来,总有惊人之处。前几天看张五常《凭栏集》,印证这个想法。他的《经济解释》最流行,我没看过,也不感兴趣,买《凭栏集》是为了里面提到书法和印章,可以送给写书法的叔叔,送前自己先看一遍(幸亏没有塑料密封),对前2/3的文章不感兴趣,甚至反感其张狂(不断引用别人表扬他的话夸奖自己,惟恐别人不知),但看到他写林风眠的一篇,立刻倾倒。
林风眠(一直欣赏大师这个名字)是广东梅县客家人,一九OO年生,少时被乡里认为是绘画天才。后来的名气,一直是国画大师,张五常却对此作惊人之语,称他为“印象派最后一位大师”。林风眠一九一九年跑到上海碰运气,考取奖学金留学巴黎。彼时印象派大师在巴黎势起,“当毕加索在巴黎大叹倒霉之际,一个梅县小子正在巴黎的艺术少林寺内尽得真传。当时外人不知道,而林风眠自己也似乎是不知道。”他回国后,经文革一劫(林亲手毁画二千,入狱四年),于七七年去港,定居太古城,好象突然心生自由,“专注于画事,一时间少年时从巴黎学得的印象派绝技表现无疑”,此前,他留下的作品都是传统国画。印象派始于十九世纪中,谁是创始者难有定论,但张五常断言,印象派终于一九九一、香港太古城,它最后的代表人是林风眠。这篇文章文字很漂亮,数语道尽大师曲折一生(他说林风眠的遭遇“是时也、命也、运也”,放在文中,极尽苍凉),我很佩服,张五常这时把自赏之语不遗余地奉送给林风眠(尽管有朋友说,那是因为林风眠不是经济学家:)。
陈丹青也是写人,写他在纽约遇到的,怀才不遇的艺术家朋友奥尔。奥尔是罗马尼亚人,恰好我妹妹大学学罗马尼亚语,虽然对这个国家一直没有好感,但对这么一个小国的艺术成就还是有点佩服的(罗马尼亚画家巴巴前年曾来中国办画展)。奥尔是那种纽约随处可见的没受过正规美术训练的画家,由于对艺术的狂热不断作画,罔顾生活,而且喜欢的是西洋古画(卢本斯)。陈丹青说他希腊式的面容俨然就是画中人,“瞧着他和他的画在一起,就像面包抹着奶酪、刀叉戳在烤牛排上那股劲!”。这个十八岁的少年,经过十数年痴心不改,用未经科班训练的不成熟技巧、一心画在纽约再没什么市场的古画。期间娶妻、生子,不停打工(竭尽全力抚养妻小),不停作画,面对画商会脸红,对着堆在画室中无法卖出的画会愤怒(被木杠戳得满脸是血)。
三十几岁的奥尔终于得以在一个阔人家做了一副墙面画,所有不成熟的技巧及激情混杂出“奇怪、动人的效果”(真想看看这副画),当然,画中希腊神话、圣经故事、罗马战役中种种角色仍然简约为他一直的模特:一家三口(书中附有奥尔及妻子斯苔芬妮的照片,二人相貌均古典、俊美)。陈丹青说是:
我仍然没说心里话。是的,我理解他,因而怜悯他的挣扎,我比他还要感谢那位房东给他机会,付钱让他疯狂;但凭什么我怜悯人家?这位‘罗马人’勇敢而无望地扮演着欧洲古典艺术的当代英雄,我尊敬他。就人种和文化而言,这理应是他的梦想。多年来我难以调和对奥尔暗藏的怜悯,现在我可以释然于心;这壁画给了我尊敬他、赞美他的机会。
来广州前,箱子里本来只放了两本书,林怀民的《云门与我》和朱天文的《花忆前身》,这下,想再放一本《艺术手册》(The Art Book),没事时看看画,虽然不懂,但艺术或说是让人感动/献身的东西,都是触类旁通的。
蔡澜的《电光幻影》,合了金庸爱用的一句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可能蔡澜就是如此看电影,复以书名嘱影迷:当作如是观。
没看到过如此跳脱的影评人,可能太久浸润行中,吃过这一行的苦,也尝过这一行的甜,作为制片人,这苦和甜可能与导演、演员的甜苦统统同归而殊途。写到电影人一节,看他懒散道来,也就是闲话家常,文字不动感情,当时情景之惊险、之感动、之幽默却又历历再现。像写成龙在南斯拉夫拍戏受伤一篇,那么高的台子,他一跳,工作人员都说动作太完美,成龙自己认为不行——一举一动不够清楚,“流”了;再一跳,够清楚,成龙认为不行——看准了目标跳,不象被人追杀,于是又跳——这一跳摔到地上,耳朵流出血来,这几下子且只是全篇铺垫,吓吓人,后来写到南斯拉夫猥琐老医生,又叫人笑——大家哪敢让那衰老头治成龙,但是情势危急来不及去别家医院,又叫陈自强打听到南斯拉夫最好的医生是彼得逊,众人大叫“我们要彼得逊医生来开刀!!”——“其貌不扬的猥琐老头微笑地对我们道:‘别紧张,我就是彼得逊医生。’”把我笑坏了,手术半途老医生且跑出来抽支烟再进去——真是个活剧。蔡澜才把笔拉回成龙身上,彼得逊说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一个病人,从他进院、照X光到动手术,血压保持一定,没有降过,真是超人,真是超人!”——蔡澜写电影人,我最喜欢这篇,两个主角互相牵带着,活了。成龙做事认真、敬业、体质超强、控制力一流,老彼医生邋遢、幽默、镇定、医术高超。该篇的结尾是:
“我们三星期后继续拍摄,不影响戏的质量,上次失败的镜头,还要来过。
成龙说。”
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描写,是说蔡澜给大岛渚当翻译一段,金马奖彩排,大岛渚在后台看着倾斜度高的塑料楼梯心里发毛,扭头对蔡澜说:“是不是大丈夫?是不是大丈夫?”(日文“大丈夫”意为“不要紧吧?”)蔡说:“当然大丈夫,我们拍外景什么山都爬过,这点小意思,大丈夫。”——“大岛觉得有理,又大点其头,嗨嗨有声。”颁奖正闷,倪匡偷偷喝酒,“道貌岸然的大岛一手将瓶子抢过去,大口吞下,速度惊人。”倪匡大笑,说:“喝酒的人,必是好人!”“大岛即又点头嗨嗨。”——大岛渚在我心目中一向是那拍《感官世界》、《战场上的快乐圣诞》的放浪不羁惊世骇俗的导演,简直于心目中都觉得他才华之余有些变态,给蔡澜一写,却像个糊涂大醉侠,“嗨嗨”之声,只见老实,不见放浪——多得蔡澜行文简洁,虽略见粗糙(港报专栏人通病),但往往重现趣景,让我在等车、排队的时候也看得下去,有这样成就的影评人,我见得不多。
从蔡澜回想我看过的一些影评集,文天祥的《影迷藏宝图》也好,陈辉扬的《梦影集》也罢,无不象论文,需要耐性,用力咀嚼。迈克写《影印本》,可读性强得多,然而太绮丽,浓得化不开,仍是要一看再看三看才好(我心里常把迈克比作柳永)。一开卷便让人笑,随时也可开始,随时也可结束的,只有蔡澜一个。虽然有时过分粗糙,但读影评,趣味耳,时时求完美只怕没的读。虽然迈克永无例外地列席我心中最爱的影评人榜首,但叫我像看晚报似随看随丢,做不到。我最贪吃,拿吃来比,迈克象生牦牛肉干,鲜艳浓缩不加调料而味道激越,吃不到也想,蔡澜就是菜根,纵有香味,仍份属家常,吃的时候高兴痛快,吃不到的时候也就忘了,想倪匡黄沾蔡澜几人友谊,不知是不是这家常味。
以上是蔡澜写电影人,虽然简略,而无不怀着悲天悯人心肠,他写电影也是这样。
有一部丑女孩莫莉?灵活(MOLLY RINGWALD,“心灵捕手”里演马特达蒙的女友,我当时惊异她的红和丑)的片子“永远”,按蔡的说法是老套又俗不可耐的故事,但“我们做观众的,要是觉得粤语残片太旧,那我们可能已经长大;但是,我们同时不能接受年轻人的片子的话,那么,我们并没有长大,我们只是丧失了赤子之心。这是多么可悲的一回事。”
给我印象深的是,蔡澜从不一意刻薄,比如写到恶心而古怪的《畸形》,也是直白地讲完故事,再加几句个人观感,而从不煽动任何读者从自己角度想问题,再比如写到法国人尚?克库图,他的诗与画是“在美之中有噩梦,噩梦之中有美”,并无主观的评判,只描述他对后世的影响力,对于读者而言,这太善解人意了——在读过的那么书里,我们从来都没缺乏过富有煽动性的热情。
他的影评我最钟爱的有两篇,一是“望乡”,通篇不象一篇影评,倒象一篇熊井启的传略,一个导演的人格和理想尽在其中,“望乡”的几个女演员倒成了配角,栗原小卷是深明大义,一力担当最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报酬还是其次;高桥洋子的戏演得自然而激烈,有裸着身子奔入院子痛苦一场,蔡澜说“戏是那么自然和必须,删剪这场戏的国家,是落后的国家。(这戏我还没看过,想象中当年必然剪了)”;田中绢代,无论在文章中还是在影史,都是当仁不让的演艺女皇,蔡澜的评语是:“无懈可击”,——电影从来都是一群人的心血。从熊井启在新加坡对日本妓女墓的凭吊,到一部反战电影的出炉,我们看到日本导演及演员的良心,蔡澜似个魅影,把阑珊往事一一在我们面前演映,我们却知道匆匆电光,并非幻影。
另一篇其实不是评电影,而是评摄影技巧,题为“该死的镜头”,英文ZOOM,蔡译“冲镜头”,能够在同一画面由远景一下“冲”成特写,或做出相反的效果。蔡澜举了个例子,说某种剧情下不是“冲”镜头能解决的,非铺车轨慢慢摇近镜头——因为“镜头的持重,才能把剧中人的感情携带出来”,看到这里我几乎有些感动,世道一直淡,蔡澜作制片应该只是管钱的,却为电影投注这么多感情,细节仍用心剖析——看他评《黄土地》,处处为影片的破绽辩解,仿佛当电影孩子一般,一个职业电影人(还是斤斤计较金钱的)能爱电影(并同时默默关注电影人,哪怕再小的配角)到这个地步诚属难得。
当然还有好多搞笑之作,象“香港喷烟机”——外国人用机器和高科技造电影烟雾,香港人用四方石油铁桶,顶一掀,烧几把拜神的香丢进去,熏一会再打开,浓烟立喷——方便快捷,又比化学药品烟雾便于扑散,叫美国同行叹为观止。搞笑时也孩子样——在我印象中的许多媒体报道上老把黄沾倪匡蔡澜几个当作搞笑老友,好象随时都能唱起黄沾与徐克合唱的那首“沧海一声笑”(在那个版里,他们还是真笑,几个破锣似的嗓子,又搞笑,又豪迈)……
某年,看烂糟糟的“Gay佬四十”,只记住了“KK”——吴镇宇的眼睛,和一个在陈小春身后背景里走过的花白头发,因为当时老觉得眼熟,却死活想不起来是谁,现在一想,扮路人都那么一本正经的,还有谁——不就是蔡澜。
玩蜻蜓
蔡澜
我们那时大家还年轻,坐在广阔的平原上等太阳。已经是秋天,芦苇长着白花,风一吹来,我们像是沉浮在白色的大海。
前一天晚上打电话打到三更,国际台还是接不通,只好放弃,但王羽把这件事挂在心上,一整天闷闷不乐。
“我不拍了。”他忽然间说,也不怕把那套全白色的戏服弄脏,一躺就躺在芦苇丛里,不见了人。
他是男主角,天皇巨星,说不拍就不拍,谁能拗他?消息传到导演张彻那里,他跺跺脚,望着天,猛抽他的雪茄。
一群人四十多人,老远地跑到日本出外景,吃住就是一大笔费用。我负责制作,处处要预防浪费,更是心急如焚。
“等收工了我再替你接电话。”我说。
“那么迟了还没有人听,你说她到哪里去了?”王羽越说越气愤。
“或者去看午夜场了吧。”
“是啊,也许是去看午夜场了。”王羽说完坐了起来。我们又有了生机。
“但是,不对呀,”他想了想,“昨晚是星期二,哪里有午夜场?”
我也说不出话来。
“会不会到朋友家去打麻将。”他为自己解答。
“对,对,打麻将。”我这么一应,他反觉不妥。
“我马上回香港。”他决定。
这事已弄得不可收拾了,有什么办法挽回?
天上飞来一群红蜻蜓,有一只停在我面前的白花上。我静悄悄地伸出手指在它的眼睛前面画圈圈。蜻蜓有复眼,圆圈越画越小,它变会头昏,等它心迷,更能一把抓住。
王羽看得神奇,也找了只蜻蜓画圆圈。一抓,让它飞走,再找来画。
大家看着这两个疯子画圆圈。郑佩佩、午马、杨志卿,甚至张彻也拿着雪茄画圆圈,把所有的事都忘却了。
太阳出来,我们继续拍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