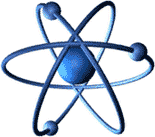Jump to navigation
Barb的不老歌
08 February
德州巴黎
迈克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他首次看《德州巴黎》(Taxes Paris),为Ry Cooder的音乐所着迷,说它“哀怨地无可奈何地在地平线那一头掠过,如一列午夜列车。它划过的地图,一个个无名的站,也有惘惘的笑,也有欲哭无泪——不是江湖是什么”,我想到的倒不是德克萨斯或巴黎,而是那犹如记忆中穿行的列车,穿过的,是我看电影的生命,纵然年轻,在影像的世界中已然苍老。
95、96那两年,在学校里,和好友次央到处看片,照她的自嘲是“像赶场一般”。两个人早上去人大旁新开的澳华影院(现在俨然成了北京最好的电影院),中午北图影院,晚上可能又换回学校图书馆的放映厅。我还记得那时看的片子是《天台的月光》、《费城》、《悲情城市》等等,那时《猜火车》还没出现。
有一次在刚开张的澳华一层小投影厅看《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堕落天使》。后者看到十几分钟的时候,人已经差不多走光了,我和次央相视一笑(我俩临别依依,怨太阳快升东——别的是电影我俩临别依依,要再见在梦中——这是我和次央),继续沉浸在哑巴阿武的喃喃自语里——摄像机里的摄像机,拍的是他老爸炒菜的镜头,我俩眼睛濡湿半晌。
又一次在学校看北影的人带来的费穆版《小城之春》,可气的是边放边讲,动不动按停,把情绪半吊在空中,老半天落不下来,待到又重新按钮,却恍惚得不知所以,恨恨地瞅着那最后也没搞清是男是女的讲解老师,终于舍下这部金玉之作,半路退场。《悲情城市》也是这样看的。中止的一刹,灯光大亮,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感觉。迈克评《悲情城市》:“一段家常的对话,一片云,一个匆匆的身影,一首歌,蕴藏着某截时间里最珍贵的记忆,串起来便成一生”。候孝贤就是如此吧,像达明一派那首久居记忆散之不去的《石头记》,闲闲听来,便是一生。
那都还是我没上网的时候,偶尔想起,上网是一个中转点,象青年到中年的转变。有了网络以后,有了这么多可以讲电影的人,但当年四处寻觅、偶遇好片子的喜悦已不复存在,从新街口到五道口,小音像店里,文得斯、塔可夫斯基、杨德昌的电影俯拾皆是。
记得以前看部《少年也安啦》,还要好友从拉萨街头拾人牙穗,巴巴地不远千里寄了来(且是录象带!),两个人在电话里都欢喜得傻乐。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好影评,看的头一秒感同身受,后来味道就渐渐淡去。好象写作人李锐说,在最浩瀚的图书馆里看到无穷无尽的藏书,顿觉写作无意义,不断又不断重复的,不知是世界哪一角落何朝何代早有先人想过做过写下的……所以令我变得不“那么爱”看电影之余,更尊敬那些仍在拍出新意的导演(这时想到的是《两杆大烟枪》和《偷抢拐骗》),甚至香港,那弹丸之地仍在坚持电影理想的导演们(这时想到的是从《香港制造》、《榴莲飘飘》到《香港有个好莱坞》,陈果的每一部影片),即使电影跌入再深的谷底,仍用声光色抚慰世上的每个寂寞角落。
年前,在广州购物中心3楼的CD店买到了《德州巴黎》的电影原声碟(广州赐我良多,短短一月,不免爱上这个城市),拿回来一听,倒抽一口凉气——恰如迈克所说,不差分毫。那恍如隔世的声音,衬着男主角一声长叹(此处想起乔纳森写海上花的《王莲生一声长叹》),冷静而苍白的声音,恰似片名传递的,生活在别处之感。此时心境,正适合套那首优客李林的歌名:电影是我一生最初苍老。
(想起《天台的月光》,就想起一件事:上个月某晚去KTV,夜半3时出来,几个朋友正为谁送谁争执时,一个要饭的小孩(约4、5岁)也掺和进来添乱,我又气又笑,叫道:“你们别拉扯了,要不这个小弟弟老跟着。”这时要饭的小孩仰起脸,用细细的声音很认真地纠正我:“阿姨,我不是小弟弟,我是小妹妹!”我一乐,眼角却瞥到一个年轻的乡下女人远远站在街角看,那是她妈妈罢?我掏出一块钱给她,小女孩高兴地谢了又谢。——这时想起《天台的月光》里,梁家辉给了“借车钱”的大陆男人钱,在片尾的时候,男人竟来还钱——他不是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