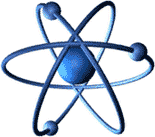Jump to navigation
Barb的不老歌
30 January
一坛醉生梦死的酒
然而还是看了王家卫。导演王家卫、摄影杜可风、美指张叔平,这三个名字像宿命般击中了我,一个又一个喃喃低语的片段,像幻灯投于白墙般于我心里留下痕迹。
95年入学后,遇见了一个可以一辈子一起说电影的人(不是家猪)。她现在在拉萨,那时在我的班里进修。就像是昨天的事,在外教Lina的家里,她坐在藤椅上,我蹲在她身边,一场又一场电影说下来,两人恨不得携手同归电影的大梦(归彼大荒)。那时我俩说得最痛快的就是《重庆森林》,因为身边没人爱看(不像《花样年华》后,王家卫一时风行,鼎鼎大名,如星巴克般灌耳)。
说到最细处,不外乎警察663坐在马桶上对香皂说:“你知不知道你瘦了?以前你胖嘟嘟的,你看你现在,都扁了,何苦呢?要对自己有信心。”对毛巾说:“我叫你不要哭嘛,你要哭到什么时候?做人要坚强一点嘛,你看看你,窝在这里象什么样子?”对毛公仔说:“怎么不说话?别生她的气了。每个人都有不清醒的时候,给她个机会,好不好?”
还有《阿飞正传》里,旭仔那“十六号,四月十六号。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号下午三点之前的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这是事实,你改变不了,因为已经过去了。明天我会再来。”
《堕落天使》中,哑巴阿武想:“每天,你都会和许多人擦肩而过,他们可能会成为你的朋友或是知己。所以我从来没有放弃和任何人擦肩而过的机会。有时候搞得自己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行了。那天晚上,我又看到了那个女人,我知道我可能不会和她成为知己或朋友。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擦肩而过,衣服都擦破了,也没有看到火花。”李嘉欣坐在摩托上,紧紧伏在他身后,“走的时候,我叫他送我回家。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摩托车了,也很久未试过这么接近一个人了,虽然我知道这条路不是很远。我知道不久我就会下车。可是,这一分钟,我觉得好暖。”
穿过了时间和空间,我相信当年很多人会从他的电影里看到自己。许多许多的感情,只是一分种擦出的火花,过后将湮灭于何处,谁会管它?
后来结识的很多爱电影的朋友,会评选自己心爱的王家卫电影,多半是自己被那片刻光影击中的一刻。《重庆森林》可能不是最好的一部,可由于95年被它击中后,受了重伤,所以它成了我最喜欢的王氏电影。其实跌进电影里面,是有点痛苦的,在活在别人故事里的不到2个小时中,生关死劫,一一感同身受。
在王家卫拍得最美的一部,《东邪西毒》里,异样苍凉的天色下,数段纷乱的感情,几个落寞的人,你,是哪一个?又或者,你是等待一句“不如重新开始”的黎耀辉,他说:“一直以为我跟何宝荣不一样,原来寂寞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一样。”
Liar曾经用“流烟非雨”这个ID写了一篇关于《东邪西毒》的文章,里面一段话他可能觉得煽情,但我喜欢:“无非是一杯清酒就可以湿透了你我的前世今生,无非是一句轻轻的爱语就可以击穿了你我的灵魂,无非是那么一段浮云掠过的情感就可以耗尽了你我的一生,无非是那么一个不再出现的身影就可以烙印在你我本来浅薄的生命。”
如他所说,这些全都是王家卫的锋芒,而王家卫身后的杜可风、张叔平,谭家明(剪辑)的光芒似至柔而隐忍,流淌在电影的每个片段中,所以不被人发觉了。《东邪西毒》里美丽的景色,我觉得无双,是《卧虎藏龙》、《英雄》都比不了的。猎猎大旗,漫漫黄沙,纠缠其中的那几个人,是张叔平的功劳了,以至以数年后周星驰在《大话西游》中仍在向盲武士致敬。还有西毒的大嫂,张曼玉那美丽的群裾,手中拈的一朵花,颊边的胭脂色,她轻轻地跟东邪说:“以前我认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有些话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一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分别,有些事会变的。我一直以为我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看着镜子,才知道我输了。在我最美好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人都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
写到这里,写不下去了,耳边只听到那几个声音……
“不久前,我遇上一个人,送给我一坛酒,她说那叫‘醉生梦死’,喝了之后,可以叫你忘掉以做过的任何事。我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酒。她说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如果什么都可以忘掉,以后的每一天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你说这有多开心。 ”
“没有事的时候,我会望向白驼山,我清楚记得曾经有一个女人在那边等着我。其实‘醉生梦死’只不过是她跟我开的一个玩笑,你越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忘记的时候,你反而记得清楚。我曾经听人说过,当你不能够再拥有,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
也许电影就是这样一坛醉生梦死的酒,你越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忘记的时候,反而记得更清楚。
28 January
浮云
《浮云》是成濑巳喜男的一部电影,曾计划去北京的雕刻时光Café看的,始终未能成行,这个名字却印在心里。想象中它是如小津安二郎的电影般波澜不惊,按关锦鹏的形容,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在有如浮云般的往事中,95年是我看电影的里程碑,正是在这一年,我清楚地发现电影于我不只是一场娱乐。香港无线电视的一位女制作人曾说过,金庸的书教她作人(忠、孝、节、义)。我的成长,我的世界观和审美观,隐约中也被电影左右着。
在95年之前,我已从电影之小中见识了世界之大,而这芥子与须弥,不亚于书。
95年以前我看到的好片子还是在电视上,很多从小说改编而来,却有一个比书更辽阔的空间,像《霍华德庄园》,像《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看了这两部电影,我不得不喜欢安东尼?霍普金斯和艾玛?汤普曼。或者,奥斯丁和哈代笔下,英国的绅士与淑女从来不是俊男与美女。只是这样平凡的样貌和无尽的隐忍,只是一个眼神,甚至只是连眼神都不敢交会的含蓄,已经让人茫茫岁月中自己只似一粒微尘。
这几个片子不是中央台看的,而是家里地方有线台,不知哪位领导突发神经,只放了一小段时间,都便宜了放假在家的我了)另两部好片子《大河恋》(A River Runs Through,罗伯特?雷德福导演)和《好人寥寥》(又翻译成《义海雄风》)也是这时看的。〈大河恋〉里第一次惊见布拉德?皮特,这个酷似雷德福(亦舒也提到过数次劳拔烈福,就是雷德福)的男孩把青春表现得再无余地,片尾华年而逝,那真是一把青春烧成了灰,导演也了无遗憾了。《好人寥寥》上个月中央台电影频道又播过,重看不免感叹汤姆克鲁斯、戴米摩尔和凯文培根当时的年轻(落花流水春去也),就连杰克?尼克尔森也不过是个中年人。过往的一出出电影,像记录片,记录着荣与衰,和这么多人曾经这么好的青春。
这中间还看了一部吓人不轻的恐怖片,《比留子》。看的时候是个下午,我一个人缩在墙角,手心流着汗,死死捏着一个枕头。这样恐怖的故事(我觉得恐怖过《午夜凶铃》)竟然有那么美的画面,且结构极严谨,让人边怕又忍不住看下去,从此对日本人的心理恐怖领教了)8O
到95年的时候,我考到了后期本科,可以到北京上学,行前,去南宁参加了一场笔会。记得真真切切,那个炎热的夏天,邕江汩汩流水声中,我看到电影院牌子上4个大字:《重庆森林》。身边有人讨论:“咦?这个名字怎么这么怪?”“我看过,一点儿也不好看,看不懂。”这一次,我和王家卫的电影失之交臂。
流年
在1995年之前,看电影完全是无意识的,而且多半是看中央台。
那时常和妈妈一起看秀兰?邓波儿系列,从《小叛逆》到《亮眼睛》。后来从报上读到这个可爱的女孩当时正受着公众无处不在的骚扰和巨大的心理压力,有点瞠目结舌。现在想想,秀兰?邓波儿该是多么一个早熟的女孩,她的十几岁似人家的一世,是把生命浓缩了来用的。
那时候的中央台每周末的国际影院真是大恩大德,老播一些在国内名气不大却真正经典的片子。我最喜欢的一个叫《一个漫长炎热的夏日》,最喜欢那个灰眼睛的男主角,眼神深到不知名远处,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叫保罗?纽曼,这部片子是他与妻子同演,得过当年的金棕榈。
另一出也是极喜欢,叫《朱门巧妇》,保罗?纽曼是豪门叛逆子,他与老爹的争执和感情戏火花四溅,伊丽莎白?泰勒是夹在其中委曲求全的女人,这出戏让我唯一一次对她有了好感。
其他的,还有《青山翠谷》(有格利高里?派克)、《费城故事》(凯瑟琳?赫本和加里?格兰特主演)、《彗星美人》(是部给天下女人看的好片)等等。那时印象最深的是每次片头21世纪福克斯的大字,以及米高梅的醒狮标志。
如果恰好有观众钟爱的片子,央视会拿来一遍一遍重映,这个名单必然包括《罗马假日》、《希茜公主》和《魂断蓝桥》。还是从言情小说上知道,那时奥黛丽?赫本的“妹妹头”在台湾曾经多么的流行。她的清丽,罗密施奈德的微笑,和费雯丽惊世的美貌,不知曾是多少男士的旧梦(“微微风,涌起旧梦,拾起一片回忆如叶落……”)。
然而怕见伤悲,我忍到很多年后才第一次看全了《魂断蓝桥》,当时却不小心看了另一出悲剧,《梦断花都》(他是记者,她是物质女子,他成名后,她堕入浮华无法自拔,渐渐理想分歧,一个夜里她醉酒夜归,他不去应门,竟致她在雪中受冻而死。当爱已成往事,他竟是没有责任的吗?)。
除了剧情片,最最感激中央台还常放另两类电影:歌舞片和希区柯克的悬疑电影。《雨中曲》不用说了,如一切旧日时光,永远是那么美。有一出印象深刻的,好象叫《红菱艳》,亦舒在小说里提过,是一个爱跳舞的少女穿上了梦想的红舞鞋,却不能停止地(恐怖地)永远地跳下去。要到这时忆起,才觉得当年好莱坞的编剧是多么好(能不忆江南!),除了梦一般的画面,竟还要灌输人思想)
希区柯克电影,是亦舒笔下女主角在夜半无事时爱看的片子,似乎也成了品味之一种,但实际上老先生的心愿是吓天下人,而不仅是白领女子:)看看《牙买加旅店》吧,那才是心理恐怖的老祖宗。《蝴蝶梦》和《煤气灯下》好象又偏浪漫了,《后窗》、《谜中谜》、《西北偏北》则带着惊悚,到了《鸟》却像走火入魔了)
前几天蒙朋友送了一本杜可风的《放色海外——非中国电影笔记》,里面记录的正是他在好莱坞重拍希氏《惊魂记》(Psycho),的经历。然而即便是他,亦无法复现大师的原貌,毕竟,陈年的煤气灯,暗夜的氤氲,旧日优雅的气息,是高科技下镁光灯再难复制的美色。
然就是杜可风,在这本书中说了我最喜欢的关于电影的一句话:电影既是亲近,又是距离,A space of a kiss。及至多年以后,我才回味过来这无限近又无限远的瞬间。那时,已在电影的梦境中一头栽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