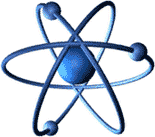Jump to navigation
Barb的不老歌
25 June
精神分裂记
最近换了新工作,忙得昏天黑地。天天加班,回家吃完东西倒头就睡,还要抽时间参加Cathayan的同学聚会、请同事朋友吃饭等等,以防自弃于世界,总之不可开交。每天早上都会看到镜子里一张懵懂肿胀的面孔,最沮丧的是磅数持续上升。
离开上一家公司时,老板送了一本书给大家,也包括我。是大卖特卖那本“奶酪”的作者Spencer Johnson写的《礼物》。我读的时候直摇头:这么简单一本小书,竟然也能赚钱?可见晕头胀脑的生活已经把人们搞到了多么狼狈的地步。
如果说“礼物”贩卖的是“专注”精神,那我早已有了——我从来不是工作狂,也不热爱工作,但是做事情的时候的确常常投入到忘我的地步,所以不知时日之飞逝。Fanfan特别同情我为什么从来遇上的都是价廉劳碌的工作,现在发现也有我自己的问题:不知不觉就多干了,干完了,甚至没察觉疲惫之将至。上周末到不爱新家玩,不爱、小船谈起网上最近很流行的奇人异事,我听得津津有味,好象刚进桃花源一样,左轻侯DD也在场,和不爱谈起钱穆等等,我又洗耳恭听,好象是恍惚间偶然进入了一个久未接触的世界,说是前世的记忆可能有点夸张,不过好象真的有点被“拖拽”回来的感觉。
上周还见到我工作后的第一位老板提姆,他老人家对我算是亦师亦友,常常在email里给我出这样那样的馊主意,其中包括:每到一个新工作岗位上都要马上开始留意和准备下一个工作机会,这话绝对只有美国人说得出来,要给中国老板们听到早就气死。这位老兄是婴儿潮时代出生的叛逆者,Cathayan非常诧异的是他老人家已经中产了这么多年,骨子里还存有那么多叛逆青年的劲头儿。我们可以说是因为电影才建立起私交的,他在中国时常常央我带他去买影碟(那时还不太会说中国话),上班的时候也常常偷偷瞒着大老板在共享文件夹里分享自己的影碟列表——他以过来人的姿态指导我,什么什么太商业啦,没有意思,为什么说哈里森福特的动作片《亡命天涯》经典啦,伯格曼的《第七封印》一定要看啦等等。从一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出他对电影耳濡目染出来的熟稔——我夸他,还是那么精神,看起来活像Henry Fonda,他马上反问,哪部电影里的Fonda?我想了想,说,是《十二怒汉》里的,他就高兴得飘了起来,很受恭维的样子,说那时的方达嘛,还是挺帅的!虽然那时候他借给我的德国片Mephisto之类常常把下班后疲惫的我看睡过去,我还是挺感谢他在电影方面给我的某些启蒙,以及share的N多八卦。
结果这次呢,吃吃喝喝之余,讨论完我的跳槽成功与否,当然要文艺一下。老人家就问我,最近看什么书,有没有看过最近著名的小说不拉不拉……我瞅了Cathayan一眼,有人证在场不好瞎编,只好很惭愧地交待道,在看杰克韦尔奇的《赢》(Winning),结果提姆那叫一个感叹,说巴巴拉你真是一个business woman啦,不过他实在不屑杰克韦尔奇,于是又讲了一堆此人的坏话八卦。我没敢说的是,我家里还搁着几本郭士纳什么的。读这些当然不是为了兴趣,也学不到什么,只是原因同前,总要开开眼,知道知道,不敢脱节于大环境。话说那天,我下班后匆匆忙忙赶去吃饭的,穿了一身职业服,和Cathayan T恤衫短裤的样子恰成鲜明对比,提姆就大吃一惊,说,挖,你怎么这么executive!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大概一向是比较多愁善感的。我也大吃一惊,好象借一面镜子看到了我自己——我不是一个懒散的文学青年吗,什么时候,也成了小时候日剧里看到的、营营役役的上班族的一员?而且对于这样的转变我自己好象也并没有什么不适应,好象温水煮青蛙,自然而然变成这样,没有发生那种理想与现实的天人交战。这只能说明,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其实你想一下这种状况就会觉得诡异——一群在公司里兢兢业业干着这样那样职业的大龄青年,坐在一起突然谈起了文史哲,虽然一点都不专业,但都正经又认真,而谈这些的前一秒钟,可能还在谈公司裁员、收购、罢工对工资的影响啦,上班离家近真是好啦什么的,简直是无缝转接。这种情形大概也只有在网上认识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时才会碰到,所以弥足珍贵,至少对于我是的。
而这时候,我的脑筋就没有不爱、小船她们那么灵光,所以有时停下来呆呆地听她们讲,倒是觉得懵然而乐。
昨天和两位初中同学聚会,喝了咖啡,回到家兴奋得睡不着,缠着Cathayan说话,他昏昏欲睡,我就自作主张非得给他念书。念的是李欧梵的《我的哈佛岁月》,讲到他那时在芝大留学饥贫交加的生活,惟音乐(CSO,芝加哥交响乐团)和电影(适逢新浪潮)给他蔚籍,其中午夜场去看特吕弗的描述(年初的《万象》上还有他一篇纪念特吕弗逝世二十年的文章,不过写得有点问题)让我很有共鸣,因为我也是特吕弗的大扇子。噢,这下才突然又想起来,我还是个影迷!当然有时在报刊亭看见《看电影》也还是买的,不过多半胡乱扔在桌子上,或者是被某人如厕时拿去看。我记得离现在最近看的碟还是Hostage,其他的新片一个也没看。又记起在看过偶像迈克纪念蒙哥马利的文章后,下定决心要抽精神好的时间看《郎心如铁》(A Place in the Sun)的,怎么竟然忘了!
再往后读,谈到李在哈佛的几位老师,研究方向的选择历程,我也是看得津津有味,觉得研究中国思想史或者是现代文学一定也很有意思——以前常在学历史的室友LHL家看到她先生(他们是同行)的许多五四时期相关的书,我只会把《良友》抽出来看看月份牌美女,对他们的专业毫无兴趣,而且很讶异他们交流起专业时的投入劲儿。那时我还很不学无术地问LHL研究这个历史有什么用处,结果被她批判为想法太“功利”(看来从那时起我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现在觉得她批判得很对。后来她去了校史研究室,求仁得仁,也很幸福。羡慕之余,我倒是很明白,这只是旁枝末节,横生出来的浪漫想法,实际上对我这样缺乏耐心的人是不可能行得通的。不过反过来,在读文艺“闲”书的时,羡慕起人家来,我好象又完全投入进去,“忘我”了。这样看来,如果我不是理想主义的,又怎能得享这些多出来的快乐。也因此,颇有点精神分裂的感觉。
不过最近胃口很好,能吃又馋,肚子饿起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为我这个天生犹疑不决的天秤座拿了主意。
上周工作忙得不但没空上网,甚至几乎忘了我还有个blog!:oops: 还是Cathayan去交域名费和收到饭饭的短信,我才突然面红耳赤地想起来,于是赶紧胡言乱语一番,算是种菜。
06 June
过关
周六送我妈上飞机,进了安检口她就完全不属于我们,她也没个手机(即使有也不舍得打长途),顺不顺利统统不得而知。周日清早终于听到电话铃声,Olimpia说终于平安地接到了妈妈。大巴到早了,她和小屁孩(听说是一爱着奇装异服的帅哥,在妹妹嘴里就变成这样)坐在侯车处等,正晃悠着脚聊天,见到某个门有个人伸进头来探头探脑,小屁孩一推她,说,哎,那是不是你妈?Olimpia一看,果然是!原来大巴到早了。
Olimpia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妈妈已经去给她洗脏碟子了。她说妈妈郁闷得不行,因为出关时被查了,所有给她带的吃的统统没收。我一听说这个噩耗,也郁闷得不行,美国电视剧里听来的以D、S、F……等等开头的字恨不得一古脑儿从我嘴里跑出来。听说以前出关时很少查住人的,有一个女王大学的老师香肠都带过。这次在贝尔法斯特出关的,除了妈妈,没有任何人被查行李,可能就她一个中国人,而且一句英国话也不会说,太显眼了。
我仔细回想都给Olim带什么好吃的了,只记起最后几天妈妈还跑了好几个地方,好不容易买到了杏干和新鲜的鱿鱼丝,她又不舍得坐车,都是顶着大太阳一袋一袋拎回来的。Olimpia说万幸中还剩下一袋牛肉丝和一包猪肉松,在贝尔法斯特接妈妈的老师骗审查员,说牛肉丝是蔬菜做的,审查员指着肉松上印的猪头说,这不明明是猪肉吗?那老师说,那是玩具的标志!据Olim观察,这俩包装上面只有拼音,没有英文,有英文的都没收了。
我们纷纷推测那人干嘛和我妈过不去,Olimpia跟我比较恶毒,说肯定是他馋了,一看见中国人就知道准有好吃的,这会儿正在家偷吃呢。我妈比较善于总结经验,说取行李时她应该把箱子上的桔红色打包带给取下来,实在太乍眼了。Cathayan不像我们这样小家烂气,伊高瞻远瞩地说,他们肯定是怕传说中的口*疫。
妈妈是从贝尔法斯特搭大巴到都柏林的,竟然郁闷得晕车了。Olimpia纳闷兼兴奋地说,我给她带的一堆影碟竟然一张也没查住。我原想她外国新片也看够了,给她弄了一堆香港日韩的,估计硬是靠方块字糊弄过去了。
咱们中国人,向来善于苦中作乐,多少无奈,一笑也就完了。妈妈很高兴路上遇见的人都说她勇敢,一个英文字不认识就大老远跑去看女儿,又笑说我们教她的“excuse me”和给她写的字条都用上了,就是在伦敦和贝尔法斯特机场找路时,人家热情地回答她的问题她听不懂,到底在机场兜了几个大圈子。
前年,我们帮过Cathayan同学的父母去签证。她是Cathayan的高中同学,她们村离Cathayan他们村不远,她去美国读书几年后,决定嫁给一个当地男孩子,请父母参加她的婚礼。她的父母都是地道的河南农民,普通话都不会讲,更不要说英文了,我们除了帮着领到签证处,帮着找住处,也帮不到什么。但老两口就这样结着伴到北京,竟然签下来,又结着伴上了美国。
这两天正看亦舒的《纵横四海》,华工为加国筑铁路的悲惨际遇及其间的传奇种种不要讲了,因故事浅,没什么标青,但说到罗四海的适应力和乐观(哪怕有时有点盲目),那真是中国人具普遍性的。为环境所迫,而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