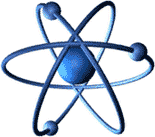Barb的不老歌
30 October
十大
一个从前和我相看两相厌的同事从马德里度假归来,带给我手信,很意外。她说感谢我给的贴士——去了我大力推荐的MM市场两次。手信是红铁皮罐,印着透纳(Turner)的画,打开是红白相间的薄荷酥糖,采办自普拉多博物馆。今天边看Mad Men边吃,想起我自己在普拉多都没顾得上买纪念品,连游览指南都没买上一本,真是黯然神伤。真想再去一次普拉多,扫荡一些El Greco的画册,再去马德里街头血拼。
但是还有那么多新奇玩意儿没有看,几时轮到旧地重游呢。从前偶尔看到一张“十大”博物馆名单——话说我很不喜欢十大头衔,不但有凑数的嫌疑,还容易误导,但毕竟先在量和地理位置上占了优势,简单扼要,适合我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客。目前只去过三家,本来很想去的大都会美术馆被Jun打消了积极性,冬宫、玛雅之类又不那么现实,所以目前梵蒂冈想去度飙升,就盼着下一个假期了。
法国卢浮宫美术馆(X)
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X)
德国柏林美术馆(X)
意大利梵蒂冈美术馆
英国大英博物馆
美国大都会美术馆
墨西哥玛雅美术馆
埃及开罗美术馆
土耳其君士坦丁美术馆
俄国冬宫博物馆
但是还有那么多新奇玩意儿没有看,几时轮到旧地重游呢。从前偶尔看到一张“十大”博物馆名单——话说我很不喜欢十大头衔,不但有凑数的嫌疑,还容易误导,但毕竟先在量和地理位置上占了优势,简单扼要,适合我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客。目前只去过三家,本来很想去的大都会美术馆被Jun打消了积极性,冬宫、玛雅之类又不那么现实,所以目前梵蒂冈想去度飙升,就盼着下一个假期了。
法国卢浮宫美术馆(X)
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X)
德国柏林美术馆(X)
意大利梵蒂冈美术馆
英国大英博物馆
美国大都会美术馆
墨西哥玛雅美术馆
埃及开罗美术馆
土耳其君士坦丁美术馆
俄国冬宫博物馆
18:11:25 -
barb -
23 October
牢骚和口水
忙得头下脚上,时间都供奉给工作,真不知道为了啥。一心念着血拼血拼血拼(我最爱的休闲活动),就是不得闲。第一,商店周日节日不开门,周六十一点开到三四点,周五开到五点——你工作的时候它也工作,你休息的时候它也休息,福利社会众生平等。第二,就算逛足五小时,把所有店铺扫荡一遍(这就是小城的好处),也找不到想要的款式颜色。I小姐报告fcuk冬天有如此这般的裙子外套,我上本城分店一看,还是瑞典人百穿不厌的黑白灰,都被买手本地化了。想跑到Lund看看Topshop,olimpia警告我,“那是年轻人穿的!”充斥大店小街城里乡间的本地货H&M或舶来品Zara虽方便,随时随地有撞衫危机,我买过两次,毫无悬念地碰见同事穿。第三,就算碰到了各方面合心意的衣服,有一半机会不合尺寸。试过一件本地规格的加小号,穿上象个布口袋,袖子长出一尺,既纳闷瑞典小个子怎么买衣服,又总算明白了我的衣服仓库UNIQLO为啥还没杀入马尔默(刚在本地商场发现无印良品,希望是前瞻信号)。
这是巴黎最让人怀念(或恐惧?)的地方,走进商店满目繁花,只怕荷包不鼓。记得和Adore一家晚饭时,混血君问,买了什么巴黎土特产没有?我们说不知买啥好。他说,有一个围巾很好的,叫XXX,这个他不会用中文发音,努力说了好几次我们才明白,原来他力荐的土产是爱玛士丝巾,差点没昏过去。同样是geek,巴黎产的也打上了不一样的烙印儿:P
刚才看黄伟文的巴黎杂记,边看边笑——因为年初读过他的斯德哥尔摩买衣记,整个一篇抱怨,说衣服样貌平庸没啥好买。这才是瑞典,没人想标新立异。巴黎才是他的宝山。
时装周的时候收到Adore短信:喂我看到了黄伟文。哪里?我们家楼下。你眼好尖啊!光头+围脖上秀过的衣服还看不出来吗。为了这个,我还在小山的指导下注册了微博,围观一下。黄先生的穿衣经不予置评,但不能不喜欢他行文家常的口吻(有点聪明,有点娇俏)和栩栩如生的细节,还有那种热心爆料的倾诉欲,好象一下子什么都新鲜热辣起来。
他在微博贴了凡尔赛一游的照片——吸引时装精法眼的自然是村上隆。他不说我都忘了,上回去的时候,的确看到新奇景象,一堆奇形怪状的雕塑,一座陈旧累赘的皇宫,不知道是谁陪衬了谁,谁提携了谁。昏昏欲睡的C同学第一次觉得当代艺术也有可取之处。

这是巴黎最让人怀念(或恐惧?)的地方,走进商店满目繁花,只怕荷包不鼓。记得和Adore一家晚饭时,混血君问,买了什么巴黎土特产没有?我们说不知买啥好。他说,有一个围巾很好的,叫XXX,这个他不会用中文发音,努力说了好几次我们才明白,原来他力荐的土产是爱玛士丝巾,差点没昏过去。同样是geek,巴黎产的也打上了不一样的烙印儿:P
刚才看黄伟文的巴黎杂记,边看边笑——因为年初读过他的斯德哥尔摩买衣记,整个一篇抱怨,说衣服样貌平庸没啥好买。这才是瑞典,没人想标新立异。巴黎才是他的宝山。
时装周的时候收到Adore短信:喂我看到了黄伟文。哪里?我们家楼下。你眼好尖啊!光头+围脖上秀过的衣服还看不出来吗。为了这个,我还在小山的指导下注册了微博,围观一下。黄先生的穿衣经不予置评,但不能不喜欢他行文家常的口吻(有点聪明,有点娇俏)和栩栩如生的细节,还有那种热心爆料的倾诉欲,好象一下子什么都新鲜热辣起来。
他在微博贴了凡尔赛一游的照片——吸引时装精法眼的自然是村上隆。他不说我都忘了,上回去的时候,的确看到新奇景象,一堆奇形怪状的雕塑,一座陈旧累赘的皇宫,不知道是谁陪衬了谁,谁提携了谁。昏昏欲睡的C同学第一次觉得当代艺术也有可取之处。

07:49:04 -
barb -
10 October
摩尔茶室
之前的旅行我也想不起来哪儿是哪儿了,因为接连去了好几个地方,有点时空错乱,只好想起一出是一出。
原来石榴在西语就叫格拉纳达(Granada),难怪连格拉纳达的水井盖上都画着石榴。多次见到石榴形小玩意儿,有布的,有瓷的,露出鲜红石榴子,很漂亮。
阿尔罕布拉宫的山脚下是老城区阿尔拜辛(Albaicin),在宫中遥望,一片白色。而在阿尔拜辛的高台回望阿尔罕布拉宫,是高高在上的赭黄色。阿尔拜辛有许多蜿蜒曲折的小路,有的窄小得不容并行,绕来绕去,看不清前面的路。有时走得全无头绪,有时又豁然开朗,露出一片广场,老人在广场闲聊乘凉。有的白房子的瓦棱和门楼和中国一式一样,怀疑是阿拉伯人传过去的。
白墙中间时有伊斯兰式门窗,时有西班牙式的蓝白瓷盘装饰,连小卖部的可口可乐招牌也做成蓝白陶瓷圆轮挂在墙上。在阿尔拜辛北面有一个古旧的吉普赛人聚居地萨克拉门托(Sacromonte),那里在山坡上开凿“窑洞”,现在开放做为参观地,多是手工作坊和佛朗明哥舞(Flamenco)表演场地——格拉纳达所在的安达露西亚(Andalusia)地区是佛朗明哥舞的原乡,但最好的舞者都在马德里,也大多在剧场表演而少去tablao(佛朗明哥舞表演场地,能边吃边看)了。最集中、水平最高的佛朗明哥表演是马德里三年一度的佛朗明哥节,今年五月适逢其盛。在夏天最好的日子,有一些举国闻名的舞者会在阿尔罕布拉宫的花园General Life做夜间演出。不用说,我都没赶上。于是特地研究了一下萨克拉门托的演出,觉得很草台,就放弃了。








阿尔拜辛大部分是居民区,不太商业化,在临近新广场的新老交界地有几条街游客鼎盛,除了饭馆酒肆土特产店这些,还有很多摩尔茶室。摩尔人原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对北非穆斯林的贬称,但就这么传下来,成为欧洲的伊斯兰征服者的代称。听说塞维利(Seville)、柯尔多巴(Cordoba)一带有清真寺套天主教堂的建筑,就是当时基督徒大战摩尔人的遗迹。
在住所附近一间茶室泡了半天——里头重帘叠幔,实际上是一个大空间用栏杆和轻纱隔出若干小空间,虽有间隔而影影绰绰。我们坐在最外头一间,座位是砌出来的砖塌,堆着锦缎垫子,靠着墙——我身后是开着的大窗,背靠窗槛,手肘刚好搁在窗台上。外面行人穿梭如织,擦着我的后背过去。这一小间有四桌,一桌空着,一个看起来流浪不知年月的男孩在抽水烟,三个讲英文的女孩子窝在一角唧喳,都恨不得缩进最暗的角落。透过眼前纱幕,仔细瞧瞧,能看见两隔之外,是另一侧沿街的窗,原来房子是两面打通的。要了两壶不知是什么的阿拉伯茶,一壶醇厚如从小喝惯的砖茶,一壶有奇特香料味,倒不难喝。一盅又一盅,灌了个半饱才发现,看上去象瓷器的粉彩茶盅,原来是玻璃的(杯子连尖嘴茶壶我都很喜欢)。他们还有各色甜腻的阿拉伯点心,因为肚子太饱没有试。


原来石榴在西语就叫格拉纳达(Granada),难怪连格拉纳达的水井盖上都画着石榴。多次见到石榴形小玩意儿,有布的,有瓷的,露出鲜红石榴子,很漂亮。
阿尔罕布拉宫的山脚下是老城区阿尔拜辛(Albaicin),在宫中遥望,一片白色。而在阿尔拜辛的高台回望阿尔罕布拉宫,是高高在上的赭黄色。阿尔拜辛有许多蜿蜒曲折的小路,有的窄小得不容并行,绕来绕去,看不清前面的路。有时走得全无头绪,有时又豁然开朗,露出一片广场,老人在广场闲聊乘凉。有的白房子的瓦棱和门楼和中国一式一样,怀疑是阿拉伯人传过去的。
白墙中间时有伊斯兰式门窗,时有西班牙式的蓝白瓷盘装饰,连小卖部的可口可乐招牌也做成蓝白陶瓷圆轮挂在墙上。在阿尔拜辛北面有一个古旧的吉普赛人聚居地萨克拉门托(Sacromonte),那里在山坡上开凿“窑洞”,现在开放做为参观地,多是手工作坊和佛朗明哥舞(Flamenco)表演场地——格拉纳达所在的安达露西亚(Andalusia)地区是佛朗明哥舞的原乡,但最好的舞者都在马德里,也大多在剧场表演而少去tablao(佛朗明哥舞表演场地,能边吃边看)了。最集中、水平最高的佛朗明哥表演是马德里三年一度的佛朗明哥节,今年五月适逢其盛。在夏天最好的日子,有一些举国闻名的舞者会在阿尔罕布拉宫的花园General Life做夜间演出。不用说,我都没赶上。于是特地研究了一下萨克拉门托的演出,觉得很草台,就放弃了。








阿尔拜辛大部分是居民区,不太商业化,在临近新广场的新老交界地有几条街游客鼎盛,除了饭馆酒肆土特产店这些,还有很多摩尔茶室。摩尔人原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对北非穆斯林的贬称,但就这么传下来,成为欧洲的伊斯兰征服者的代称。听说塞维利(Seville)、柯尔多巴(Cordoba)一带有清真寺套天主教堂的建筑,就是当时基督徒大战摩尔人的遗迹。
在住所附近一间茶室泡了半天——里头重帘叠幔,实际上是一个大空间用栏杆和轻纱隔出若干小空间,虽有间隔而影影绰绰。我们坐在最外头一间,座位是砌出来的砖塌,堆着锦缎垫子,靠着墙——我身后是开着的大窗,背靠窗槛,手肘刚好搁在窗台上。外面行人穿梭如织,擦着我的后背过去。这一小间有四桌,一桌空着,一个看起来流浪不知年月的男孩在抽水烟,三个讲英文的女孩子窝在一角唧喳,都恨不得缩进最暗的角落。透过眼前纱幕,仔细瞧瞧,能看见两隔之外,是另一侧沿街的窗,原来房子是两面打通的。要了两壶不知是什么的阿拉伯茶,一壶醇厚如从小喝惯的砖茶,一壶有奇特香料味,倒不难喝。一盅又一盅,灌了个半饱才发现,看上去象瓷器的粉彩茶盅,原来是玻璃的(杯子连尖嘴茶壶我都很喜欢)。他们还有各色甜腻的阿拉伯点心,因为肚子太饱没有试。


11:44:57 -
barb -
08 October
照片、闹学记及猪肉丝
试着翻了一下我认为惊艳的照片——也许别人不这么认为。我一向喜欢,呃,那种南洋的调调。当然翻拍后效果差了很多。

话说前天C同学在家大宴英语班的同学,巴西大妈及其子、西班牙小伙及智利小伙各一名,立陶宛美女二位,印尼大姐一名。大家混乱地吃了一顿晚饭——我们家是标准二人公寓,各种用具都是二人份,七拼八凑好不容易都坐得下、吃得上。大家却是很愉快地,就着一瓶伏特加,操着半吊子英语胡侃。这一班人,连爱尔兰老师,一时去烤肉,一时去卡拉OK,平时最讨厌泡咖啡馆的C同学也肯跟人去喝咖啡,同窗的威力好大。他每次眉飞色舞地跟我描述同学们的课堂表现(西班牙小伙安德烈课堂作文:马德里女孩夏天穿得象bitch——老师痛批),我就想起《闹学记》,我甚至记得一些篇名,“如果教室像游乐场”、“春天不是读书天”。
和安德烈说起“猪肉丝”(churros),给他看照片(直棍西班牙油条),他说不不不,这不是churros,这是porras。那猪肉丝是什么?他找出照片一看,原来是弄弯后两头接在一起的油条。我说它们有啥区别,难道味道不一样?他认真地说,味道是一样的,但是形状不一样,弯的叫churros,直的叫porras……难道只有我们中国人掌握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真谛?(羊肉猪肉牛肉鸡肉,洋人要四个词,对于中国人,管它是谁的,不都是肉嘛。)

左边是porras,右边是churros

话说前天C同学在家大宴英语班的同学,巴西大妈及其子、西班牙小伙及智利小伙各一名,立陶宛美女二位,印尼大姐一名。大家混乱地吃了一顿晚饭——我们家是标准二人公寓,各种用具都是二人份,七拼八凑好不容易都坐得下、吃得上。大家却是很愉快地,就着一瓶伏特加,操着半吊子英语胡侃。这一班人,连爱尔兰老师,一时去烤肉,一时去卡拉OK,平时最讨厌泡咖啡馆的C同学也肯跟人去喝咖啡,同窗的威力好大。他每次眉飞色舞地跟我描述同学们的课堂表现(西班牙小伙安德烈课堂作文:马德里女孩夏天穿得象bitch——老师痛批),我就想起《闹学记》,我甚至记得一些篇名,“如果教室像游乐场”、“春天不是读书天”。
和安德烈说起“猪肉丝”(churros),给他看照片(直棍西班牙油条),他说不不不,这不是churros,这是porras。那猪肉丝是什么?他找出照片一看,原来是弄弯后两头接在一起的油条。我说它们有啥区别,难道味道不一样?他认真地说,味道是一样的,但是形状不一样,弯的叫churros,直的叫porras……难道只有我们中国人掌握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真谛?(羊肉猪肉牛肉鸡肉,洋人要四个词,对于中国人,管它是谁的,不都是肉嘛。)

左边是porras,右边是churros
21:36:41 -
barb -
05 October
三毛
最近胡乱看书,喜欢的不知从何说起,不喜欢的倒常想唠叨几句。刚翻完一本三毛画传,满纸车轱辘话,充满抄来问来自相矛盾的片段,有拼凑骗钱嫌疑。不过确实有一些以前没看过的图片,有一张简直惊艳,少女三毛窝在花沙发上,穿着低胸吊带背心,黄色超短裙,都是碎花的,充满南洋风情(就象《新不了情》),她扭头看着别处,尖下颌,眼睛象翁美玲那么大。搜索了一下没找到这张照片。
我不算三毛粉丝,不过她的书差不多都看过。好象不少是我妈从学校图书室拿回来的,友谊版,大概都没付过版税。很小的时候,觉得学校生活灰暗没有出头之日的时候,看过她的书,心里还在想,台湾学生怎么比我们还惨。后来我的很要好的朋友还跟我说,初二时他们男生打打闹闹,忽然看到我课斗里有一本三毛的书,很吃惊,心想她怎么看这么高深的书。成年之后知道笑死了。结果反而是这个朋友后来迷上了三毛,有过不少反抗体制的行径。他在毕业纪念册上的理想一栏填的是,天涯拾荒去。
这次边看这个画传,边跟不知三毛为何物的C同学说,三毛很厉害啊,一九七几年就跑到北非和南美,十几岁就去西班牙读书。C同学说,那还挺有钱。真是,以前看她写逃离学校的惨烈,并没想到实在是家境允许她与众不同。连催着先生搬到沙漠去实现梦想,也提着一枕套父母给的津贴。
朱天心说得好,三毛实则是个演员,她在生活中寻找戏剧,而且热衷于扮演角色。我想起她的一些书,实在是很戏剧腔的,过分快乐和热烈,完全不象真的。好象小丑,你不知道他的笑脸下是什么面目。这个人一直为了别人的认同活着——累病了还拼命回读者信,演讲,参加金马奖应酬,虽然自己嘴上说不愿意——难怪有一天活不下去了。
至于她和荷西感情到底好不好的争议,当然不重要。不过从种种段落看得出来,一个老实巴交的工科男,一个就爱讲精神层面的文艺女,一个得承受二人生活的重压,一个只须作家庭主妇还有家庭资助……经济压力和价值观差异摆在那儿,有矛盾完全可以想象。好象作者和当时的读者都不允许把一对神仙眷侣的佳话放进人间。
并不是说她不好,我至今喜欢她的书《万水千山走遍》,中南美洲至今也不是中国人普遍的旅游目的地,她是先行官。我喜欢她写《大蜥蜴之夜》,对环境的极度敏感和油画一样浓重的描述。也喜欢她写《朝阳为谁》和顾福生学画,内心与外界鲜明如明暗对比。她的文字是绘画一样的文字,可惜并没随着广泛的阅读增加深度。以至于她最受欢迎的两本书《撒哈拉的故事》和《哭泣的骆驼》象浓缩药水,用了又用,直到稀薄了,生命也黯然无光。虽然没看过《滚滚红尘》,也觉得编剧这个活儿对她可一不可二,因为积累不够,很快就掏空了。她是感受型的,很被动,不是创造型的——港台很多创作人有这个毛病。
如果我是现在这个年纪看她的书,不一定看得进去(她实在太自恋了)。但是我是十一二岁,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年纪,开始看她的书,以至成为童年记忆的一部分,所以走在马德里这样的地方,看到美术馆的画,自然而然就想起她。

我不算三毛粉丝,不过她的书差不多都看过。好象不少是我妈从学校图书室拿回来的,友谊版,大概都没付过版税。很小的时候,觉得学校生活灰暗没有出头之日的时候,看过她的书,心里还在想,台湾学生怎么比我们还惨。后来我的很要好的朋友还跟我说,初二时他们男生打打闹闹,忽然看到我课斗里有一本三毛的书,很吃惊,心想她怎么看这么高深的书。成年之后知道笑死了。结果反而是这个朋友后来迷上了三毛,有过不少反抗体制的行径。他在毕业纪念册上的理想一栏填的是,天涯拾荒去。
这次边看这个画传,边跟不知三毛为何物的C同学说,三毛很厉害啊,一九七几年就跑到北非和南美,十几岁就去西班牙读书。C同学说,那还挺有钱。真是,以前看她写逃离学校的惨烈,并没想到实在是家境允许她与众不同。连催着先生搬到沙漠去实现梦想,也提着一枕套父母给的津贴。
朱天心说得好,三毛实则是个演员,她在生活中寻找戏剧,而且热衷于扮演角色。我想起她的一些书,实在是很戏剧腔的,过分快乐和热烈,完全不象真的。好象小丑,你不知道他的笑脸下是什么面目。这个人一直为了别人的认同活着——累病了还拼命回读者信,演讲,参加金马奖应酬,虽然自己嘴上说不愿意——难怪有一天活不下去了。
至于她和荷西感情到底好不好的争议,当然不重要。不过从种种段落看得出来,一个老实巴交的工科男,一个就爱讲精神层面的文艺女,一个得承受二人生活的重压,一个只须作家庭主妇还有家庭资助……经济压力和价值观差异摆在那儿,有矛盾完全可以想象。好象作者和当时的读者都不允许把一对神仙眷侣的佳话放进人间。
并不是说她不好,我至今喜欢她的书《万水千山走遍》,中南美洲至今也不是中国人普遍的旅游目的地,她是先行官。我喜欢她写《大蜥蜴之夜》,对环境的极度敏感和油画一样浓重的描述。也喜欢她写《朝阳为谁》和顾福生学画,内心与外界鲜明如明暗对比。她的文字是绘画一样的文字,可惜并没随着广泛的阅读增加深度。以至于她最受欢迎的两本书《撒哈拉的故事》和《哭泣的骆驼》象浓缩药水,用了又用,直到稀薄了,生命也黯然无光。虽然没看过《滚滚红尘》,也觉得编剧这个活儿对她可一不可二,因为积累不够,很快就掏空了。她是感受型的,很被动,不是创造型的——港台很多创作人有这个毛病。
如果我是现在这个年纪看她的书,不一定看得进去(她实在太自恋了)。但是我是十一二岁,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年纪,开始看她的书,以至成为童年记忆的一部分,所以走在马德里这样的地方,看到美术馆的画,自然而然就想起她。

18:16:15 -
barb -
04 October
宫娥
ffy提到老张老杨二老参观普拉多时对委拉斯开兹(Diego Velasquez)的《宫娥》(Las Meninas)印象很深,倒是提醒我了。还没看到《宫娥》原作前,先在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看到无数仿作——没错,就这一幅,毕加索画了一屋子,一幅还没画完又来一幅,简直是疯魔了。画中的小公主玛格丽特在远景近景神出鬼没有时又自成一体,常常阴阳脸,硬裙子又色彩各异,看起来象一个反复出现在疯狂梦魇中的小魔怪。看得出来画家是焦急的,急于获取委拉斯开兹布置空间的奥秘。

看到委拉斯开兹的原作,最大的感受是微妙的时空感:平衡在被打破和复原之间的一瞬间。画家在给国王王后画像,侏儒正弄狗,小公主闯了进来,好象带来一缕风。宫娥要服侍慰问她,小公主却很漠然,和画家于明暗两际独立于现世之外。委拉斯开兹还有好几幅画玛格丽特的肖像(没在普拉多看到,或许藏在奥地利),有的穿玫瑰色裙子,有的穿白色,她美丽倨傲而冷漠——看起来也就象个小魔怪。他笔下的另一位公主,玛格丽特的姐姐玛丽亚,就温柔娴静得多,但也温吞木讷,没啥个性。

除了毕老先生,《宫娥》和玛格丽特还被无数当代艺术家恶搞过,比如法国摄影师Gérard Rancinan的颠覆照片、日本人森村泰昌(Yasumasa Morimura)的易装照。

by Gérard Rancinan
这是戏仿《宫娥》的时装广告(仍然搞不清是哪一家),摄影师自比委拉斯开兹。

马德里Reina Sofia中心到提森博物馆的路上有家纪念品店,抬头一看,二楼栏杆就摆着假人宫娥与公主。


看到委拉斯开兹的原作,最大的感受是微妙的时空感:平衡在被打破和复原之间的一瞬间。画家在给国王王后画像,侏儒正弄狗,小公主闯了进来,好象带来一缕风。宫娥要服侍慰问她,小公主却很漠然,和画家于明暗两际独立于现世之外。委拉斯开兹还有好几幅画玛格丽特的肖像(没在普拉多看到,或许藏在奥地利),有的穿玫瑰色裙子,有的穿白色,她美丽倨傲而冷漠——看起来也就象个小魔怪。他笔下的另一位公主,玛格丽特的姐姐玛丽亚,就温柔娴静得多,但也温吞木讷,没啥个性。

除了毕老先生,《宫娥》和玛格丽特还被无数当代艺术家恶搞过,比如法国摄影师Gérard Rancinan的颠覆照片、日本人森村泰昌(Yasumasa Morimura)的易装照。

by Gérard Rancinan
这是戏仿《宫娥》的时装广告(仍然搞不清是哪一家),摄影师自比委拉斯开兹。

马德里Reina Sofia中心到提森博物馆的路上有家纪念品店,抬头一看,二楼栏杆就摆着假人宫娥与公主。

22:16:32 -
barb -
03 October
奥塞美术馆
在巴黎看过奥塞(d'Orsay)美术馆,因为有点失望,说了句觉得奥塞不如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结果引起误会,赶紧记录当时的感想澄清一下。骄傲的巴黎人大抵不允许人说奥塞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之一,就象不允许人说凡尔塞宫不漂亮一样。虽然比起奥塞我仍然更喜欢普拉多,所幸美术馆们根本不会因为谁喜欢或不喜欢它们而稍作任何改变。
我欣赏奥塞的因地制宜和实用,把火车站改成美术馆,高阔的空间任人自由徜徉冥想——大厅中间的雕塑区常有人坐着发呆,有的用目光抚触雕像,有的完全沉浸进自己的内心世界。顶棚透露天光,天空高阔的时候,心情也自然跟着高阔起来。一般巴黎馆员都是很高傲的,他们担负着喝止游客照相的重任。其中一位正要阻拦一个美国老头拍照,老头争辩说,我只是想拍一下这座大钟,它和我们家乡火车站的大钟看着实在是象啊,结果馆员笑了,高兴地说就是仿那个造的,不但不阻止照相,还聊起天来,露出人情味的一面。
在奥塞呆了六个钟头,细细看了一遍。很喜欢梵高的小展——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千头万绪,太密集了,多新奇高妙的作品一下重复一千次也受不了。二三十幅恰足以使人留下迅速精炼的印象——尤其他的一幅自画像,不戴帽子,未割耳朵,天青色背景的一幅,我很喜欢。他把自己作为一个旁人剖析,又用刮刀表达这个剖析的结果,仿佛在问,你认同这个分析吗?

库尔贝(Gustave Courbet)的大画占了一大片。在卢浮宫游逛的时候,我就对超级尺寸的西班牙、法国大画避之则吉,除了感慨画的时候有多费劲,简直没有任何感觉。我并不是讨厌写实主义,只是他黑暗凌乱的人物总有一种政治意味,名为表现现实,画家本人的优越感却凌驾于画面之上,人物还很造作,总之无感。
另有一些表现农村生活的画非常不合逻辑。譬如波纳(Rosa Bonheur)最著名的春耕图(The First Dressing),画农夫驱牛犁地,牛低头奋蹄,画得本来很好,可是我找遍了画里八九头牛身上都不见绳索鼻环——这犁是怎么神奇无形地拴在牛身上的呢?后来碰见C同学,一说起来两人一是模一样的疑惑。另有一幅布列东(Jules Breton)画的《拾穗者之归》(Calling in the Gleaners),花容月貌的农家女们赤脚站在麦地里拾穗——麦茬不早就把脚板扎烂了吗?
二人均属高喊到乡间去的巴比松画派——可见艺术青年画农活是一种理想主义。这可不是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
比较有趣的倒是巴比松画派的摄影展——有的近拍小草花叶,象现在用卡片机一样随心所欲,可是那是十九世纪末,照相仍为昂贵的技术。以乡间风景为贵的巴比松派画家莫非都是富家公子?
奥塞是印象派画作的集散地,印象派又是巴黎土特产,难怪本地人如此引它为傲。我并不特别是印象派的粉丝,好象各个年代画派,都有手段高超的画家,使人为之钟情,印象派只是由于时代的渊源而产生的其中一支。而好画家又常常多变,喜欢一个时期的不一定喜欢另一个时期,喜欢一幅作品而憎恶另一幅作品,也是常有的事。奥塞虽有众多马奈、莫奈、雷诺阿、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希斯莱(Alfred Sisley)……奈何除了梵高的自画像和麦田小憩,没有我特别想看的几幅,比如莫奈的莲池和雷诺阿的弹琴姐妹(这些后来都在橘园美术馆看到,容后再讲)。
奥塞藏的印象派画作中最丰盛的是德加,不但有画,还有雕塑。虽然画芭蕾舞女出名的画家只有这么一个,但我还是得说,他所画不及真实世界十分之一。就连中芭的排练室,还要更明亮、更轻盈些呢,何况他身边的歌剧院芭蕾舞团。在歌剧院参观时,见到首席舞者们着时装的照片,看在我的眼里犹如谪仙。因此瞧不出德加绘画的好处——可是,很喜欢他作的雕塑芭蕾少女(Little Dancer),十四岁的小女孩背着手微微仰头,做了一个起手式,舞裙和发带都是纱布做的,有一种纯真飞扬的神气。因为喜欢,特地买了纪念品给某小姐做礼物。
老实说,看过奥塞,我几乎对印象派是失望的,一代翻天覆地的革命仅止于此?由于印象派的崛起,淹没了多少当时技法高超的传统画家(尤其一些现在不知名的美国画家)。年少时看张五常写林风眠的《印象派终于太古城》是多么荡气回肠……
事实证明不能在没有全面了解时仓促下结论——在巴黎最后一天去了小美术馆橘园,在那里总算又燃起对印象派的小火焰,一回来就翻出美国人约翰雷华德(John Rewald)的《印象派绘画史》看(先解一下老实人梵高为何与高更这种家伙交好的大谜题,我8卦地想)。
恩,再倒回来说说喜欢奥塞的地方:
有一些马蒂斯之外的野兽派画家的作品,色彩很美,比如安德列德兰(André Derain)。看到成块鲜绿明黄有如燃烧一般的秋天景色,我就想起三毛写到跟顾福生学画时,把油彩弄到毛衣上干脆连毛剪掉的情景。
乔治修拉的点画《马戏团》(The Circus)很美,那种精准的平衡,让人想起安格尔(Ingres)。他用色虽然也轻柔,但比安格尔明亮鲜艳多了,有一种轻盈嬉戏的感觉。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才恋恋不舍地走掉。我们卧室的书柜里一直摆着Olimpia的同学S小姐送的一副修拉的印刷品,《大碗岛上的星期日》(A Sunday Afternoon on the Island of La Grande,现藏芝加哥艺术学院),走的是同一种精雕细作的路子。

歌剧院舞台布景展览——纸板的罗密欧朱丽叶的场景,又有歌剧院的侧面解剖图,从服装室、机械室、道具室、到舞台、观众席,不一而足,是参观加尼耶歌剧院极好的补充,不知道为什么不干脆在歌剧院一块展了算了。
新艺术风格的家具,其中有巴黎地铁入口的设计师季玛赫(Hector Guimard)设计的满堂家具,感觉很神奇。巴黎的老地铁入口是一个圆弧形的铁栏,很多还在使用,上面伸出两只大灯,夜间象怪兽的两只大眼睛(以前还专门搬到北京展出过一次)。现在一看到这些家具,马上知道出自同一人之手——这种设计上的“血缘”真是很神奇。好象也是Jun说的,艺术这东西么,不在于技巧多高超,顶重要是风格,是特别。不过这些家具比起地铁站实用性就差多了,非全套放在天高地阔的城堡里不足以凸显其“艺术性”的一气呵成。

Guimard设计的地铁入口(图片来自Anthony's Home Page)
还有一个遗憾:没看到极想看的一幅画,Gustav Caillebotte的《刨木工》(The Floor Scrapers),不知道是借出了还是我没找到。名编舞Angelin Preljocaj曾以它为灵感编过一支舞,由希西寇拉(Cyril Collard)拍入电影《夜夜夜狂》(Les nuits fauves)里,三者我都想看。

我欣赏奥塞的因地制宜和实用,把火车站改成美术馆,高阔的空间任人自由徜徉冥想——大厅中间的雕塑区常有人坐着发呆,有的用目光抚触雕像,有的完全沉浸进自己的内心世界。顶棚透露天光,天空高阔的时候,心情也自然跟着高阔起来。一般巴黎馆员都是很高傲的,他们担负着喝止游客照相的重任。其中一位正要阻拦一个美国老头拍照,老头争辩说,我只是想拍一下这座大钟,它和我们家乡火车站的大钟看着实在是象啊,结果馆员笑了,高兴地说就是仿那个造的,不但不阻止照相,还聊起天来,露出人情味的一面。
在奥塞呆了六个钟头,细细看了一遍。很喜欢梵高的小展——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千头万绪,太密集了,多新奇高妙的作品一下重复一千次也受不了。二三十幅恰足以使人留下迅速精炼的印象——尤其他的一幅自画像,不戴帽子,未割耳朵,天青色背景的一幅,我很喜欢。他把自己作为一个旁人剖析,又用刮刀表达这个剖析的结果,仿佛在问,你认同这个分析吗?

库尔贝(Gustave Courbet)的大画占了一大片。在卢浮宫游逛的时候,我就对超级尺寸的西班牙、法国大画避之则吉,除了感慨画的时候有多费劲,简直没有任何感觉。我并不是讨厌写实主义,只是他黑暗凌乱的人物总有一种政治意味,名为表现现实,画家本人的优越感却凌驾于画面之上,人物还很造作,总之无感。
另有一些表现农村生活的画非常不合逻辑。譬如波纳(Rosa Bonheur)最著名的春耕图(The First Dressing),画农夫驱牛犁地,牛低头奋蹄,画得本来很好,可是我找遍了画里八九头牛身上都不见绳索鼻环——这犁是怎么神奇无形地拴在牛身上的呢?后来碰见C同学,一说起来两人一是模一样的疑惑。另有一幅布列东(Jules Breton)画的《拾穗者之归》(Calling in the Gleaners),花容月貌的农家女们赤脚站在麦地里拾穗——麦茬不早就把脚板扎烂了吗?
二人均属高喊到乡间去的巴比松画派——可见艺术青年画农活是一种理想主义。这可不是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
比较有趣的倒是巴比松画派的摄影展——有的近拍小草花叶,象现在用卡片机一样随心所欲,可是那是十九世纪末,照相仍为昂贵的技术。以乡间风景为贵的巴比松派画家莫非都是富家公子?
奥塞是印象派画作的集散地,印象派又是巴黎土特产,难怪本地人如此引它为傲。我并不特别是印象派的粉丝,好象各个年代画派,都有手段高超的画家,使人为之钟情,印象派只是由于时代的渊源而产生的其中一支。而好画家又常常多变,喜欢一个时期的不一定喜欢另一个时期,喜欢一幅作品而憎恶另一幅作品,也是常有的事。奥塞虽有众多马奈、莫奈、雷诺阿、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希斯莱(Alfred Sisley)……奈何除了梵高的自画像和麦田小憩,没有我特别想看的几幅,比如莫奈的莲池和雷诺阿的弹琴姐妹(这些后来都在橘园美术馆看到,容后再讲)。
奥塞藏的印象派画作中最丰盛的是德加,不但有画,还有雕塑。虽然画芭蕾舞女出名的画家只有这么一个,但我还是得说,他所画不及真实世界十分之一。就连中芭的排练室,还要更明亮、更轻盈些呢,何况他身边的歌剧院芭蕾舞团。在歌剧院参观时,见到首席舞者们着时装的照片,看在我的眼里犹如谪仙。因此瞧不出德加绘画的好处——可是,很喜欢他作的雕塑芭蕾少女(Little Dancer),十四岁的小女孩背着手微微仰头,做了一个起手式,舞裙和发带都是纱布做的,有一种纯真飞扬的神气。因为喜欢,特地买了纪念品给某小姐做礼物。
老实说,看过奥塞,我几乎对印象派是失望的,一代翻天覆地的革命仅止于此?由于印象派的崛起,淹没了多少当时技法高超的传统画家(尤其一些现在不知名的美国画家)。年少时看张五常写林风眠的《印象派终于太古城》是多么荡气回肠……
事实证明不能在没有全面了解时仓促下结论——在巴黎最后一天去了小美术馆橘园,在那里总算又燃起对印象派的小火焰,一回来就翻出美国人约翰雷华德(John Rewald)的《印象派绘画史》看(先解一下老实人梵高为何与高更这种家伙交好的大谜题,我8卦地想)。
恩,再倒回来说说喜欢奥塞的地方:
有一些马蒂斯之外的野兽派画家的作品,色彩很美,比如安德列德兰(André Derain)。看到成块鲜绿明黄有如燃烧一般的秋天景色,我就想起三毛写到跟顾福生学画时,把油彩弄到毛衣上干脆连毛剪掉的情景。
乔治修拉的点画《马戏团》(The Circus)很美,那种精准的平衡,让人想起安格尔(Ingres)。他用色虽然也轻柔,但比安格尔明亮鲜艳多了,有一种轻盈嬉戏的感觉。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才恋恋不舍地走掉。我们卧室的书柜里一直摆着Olimpia的同学S小姐送的一副修拉的印刷品,《大碗岛上的星期日》(A Sunday Afternoon on the Island of La Grande,现藏芝加哥艺术学院),走的是同一种精雕细作的路子。

歌剧院舞台布景展览——纸板的罗密欧朱丽叶的场景,又有歌剧院的侧面解剖图,从服装室、机械室、道具室、到舞台、观众席,不一而足,是参观加尼耶歌剧院极好的补充,不知道为什么不干脆在歌剧院一块展了算了。
新艺术风格的家具,其中有巴黎地铁入口的设计师季玛赫(Hector Guimard)设计的满堂家具,感觉很神奇。巴黎的老地铁入口是一个圆弧形的铁栏,很多还在使用,上面伸出两只大灯,夜间象怪兽的两只大眼睛(以前还专门搬到北京展出过一次)。现在一看到这些家具,马上知道出自同一人之手——这种设计上的“血缘”真是很神奇。好象也是Jun说的,艺术这东西么,不在于技巧多高超,顶重要是风格,是特别。不过这些家具比起地铁站实用性就差多了,非全套放在天高地阔的城堡里不足以凸显其“艺术性”的一气呵成。

Guimard设计的地铁入口(图片来自Anthony's Home Page)
还有一个遗憾:没看到极想看的一幅画,Gustav Caillebotte的《刨木工》(The Floor Scrapers),不知道是借出了还是我没找到。名编舞Angelin Preljocaj曾以它为灵感编过一支舞,由希西寇拉(Cyril Collard)拍入电影《夜夜夜狂》(Les nuits fauves)里,三者我都想看。

16:11:11 -
barb -
02 October
墓园
今天去Lund和lastrada小姐会面——最近总和大家提到相识几年这个话题,真是年事渐高——我们认识大概也有六七年了,总是缘悭一面,我刚搬来瑞典的时候她在波士顿,她回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我又在四处游玩,这下总算随遇而安地见到了。
吃完饭想去植物园,迷路进了一片墓地。L小姐很高兴,拍照留念。我赶紧问在巴黎去公墓没有,她说连拉雪兹、蒙马特去了三座。“我收集墓园”,她是这样说。刚刚去看了L小姐拍过的墓园,都很美。
我在巴黎没有专门去墓园,虽然一直都喜欢去——刚搬到马尔默的时候,中介马丁带我们找房子,特地如风景名胜一样向我们指出来,那里这里有一处墓园。我那时不要住在墓园旁边,但是后来非常的喜欢上宁静的墓地,风格迥异的墓碑,常去散步。留意墓碑上的名字和生卒年月,背后都有故事。离我家一站地的墓园,甚至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于一九八几年下葬,名字和一位香港导演相似。
五月的时候墓园草长莺飞,有的碑前点着长明灯,有的栽着花树。古斯塔夫广场那里有古老的一座,因为开阔宽敞,成了行人的捷径(沉睡的人于是不应寂寞)。春天冰雪消融,也是墓园最早开出雪花莲。
今晚回来请同事姬丝蒂娜和她的男朋友菲力普吃饭(同在我们公司工作的菲力普刚被中国女同事们评为头号帅哥,恭喜他),大家原来都很喜欢墓园。菲力普说他家附近那座墓园最边际有吉普塞人的墓穴,叫我们去看。又说Lund那片墓地,名为学者之墓,非名士大儒不得“入住”。
吃完饭想去植物园,迷路进了一片墓地。L小姐很高兴,拍照留念。我赶紧问在巴黎去公墓没有,她说连拉雪兹、蒙马特去了三座。“我收集墓园”,她是这样说。刚刚去看了L小姐拍过的墓园,都很美。
我在巴黎没有专门去墓园,虽然一直都喜欢去——刚搬到马尔默的时候,中介马丁带我们找房子,特地如风景名胜一样向我们指出来,那里这里有一处墓园。我那时不要住在墓园旁边,但是后来非常的喜欢上宁静的墓地,风格迥异的墓碑,常去散步。留意墓碑上的名字和生卒年月,背后都有故事。离我家一站地的墓园,甚至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于一九八几年下葬,名字和一位香港导演相似。
五月的时候墓园草长莺飞,有的碑前点着长明灯,有的栽着花树。古斯塔夫广场那里有古老的一座,因为开阔宽敞,成了行人的捷径(沉睡的人于是不应寂寞)。春天冰雪消融,也是墓园最早开出雪花莲。
今晚回来请同事姬丝蒂娜和她的男朋友菲力普吃饭(同在我们公司工作的菲力普刚被中国女同事们评为头号帅哥,恭喜他),大家原来都很喜欢墓园。菲力普说他家附近那座墓园最边际有吉普塞人的墓穴,叫我们去看。又说Lund那片墓地,名为学者之墓,非名士大儒不得“入住”。
23:49:50 -
barb -
01 October
早午晚餐
一写到吃的就停不住手。
在西班牙马不停蹄,仍然不放过每一个吃的机会。离开巴塞罗那前一天晚上,在旅馆对面的tapas店一口气吃了七八碟——头一天半夜被他家的人来人往吵到,终于扛不住诱惑走进去,事实证明是英明的抉择。每样都好吃,连看着最不起眼的煎香肠(chorizo)都好吃得要把舌头吞下去。滚烫的油炸茄子饼也很美味,又脆又香,西班牙人做茄子无疑比希腊人高一个段位。最激动人心的是墨鱼,在橄榄油和蒜末里煎熟,又弹牙又清爽,再挤两滴柠檬,哗,整个味觉飘升到天上去了。感觉象大餐,不象小吃。
午餐因为总是在去往哪儿的路上,所以比较凑合,偶尔吃过一次海鲜饭paella,觉得饭是夹生的,很不喜欢。后来听Olimpia说并不是做的不好,而是这饭就这个吃法。米只炒不焖,在中国人嘴里总归不够火候。遂想起btsb作为爱吃米的中国人在挪威得到的特殊礼遇:沙拉里拌上生大米。
倒是就着啤酒吃的橄榄很不错。有红有绿,参差皴裂,看着象豆子。吃起来也象豆子,软软的,不太咸,嘴一抿吐出核,留下橄榄的清香。一颗不停地吃个精光。
因为不活动胃口不开,早晨吃不下味道太重的东西,所以虽然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老咖啡馆选择众多,一直没找到可心的早点,直到在马拉加吃了清爽的烤面包夹火腿——火腿是咸的但只有薄薄一片,配一碟番茄碎和一包橄榄油,随便搭配。最有趣的是点好后服务员要问你的名字——餐好了,麦克风大叫一声“芭芭拉”,赶紧跳起来去接——在异国他乡陌生餐馆里回荡自己的名字这还是头一遭。于是边吃早点,边自然而然知道了排在我后面的帅哥芳名“雅各布”。



晚餐(巴塞罗那)


午餐(格拉纳达)和早餐(马拉加)
在西班牙马不停蹄,仍然不放过每一个吃的机会。离开巴塞罗那前一天晚上,在旅馆对面的tapas店一口气吃了七八碟——头一天半夜被他家的人来人往吵到,终于扛不住诱惑走进去,事实证明是英明的抉择。每样都好吃,连看着最不起眼的煎香肠(chorizo)都好吃得要把舌头吞下去。滚烫的油炸茄子饼也很美味,又脆又香,西班牙人做茄子无疑比希腊人高一个段位。最激动人心的是墨鱼,在橄榄油和蒜末里煎熟,又弹牙又清爽,再挤两滴柠檬,哗,整个味觉飘升到天上去了。感觉象大餐,不象小吃。
午餐因为总是在去往哪儿的路上,所以比较凑合,偶尔吃过一次海鲜饭paella,觉得饭是夹生的,很不喜欢。后来听Olimpia说并不是做的不好,而是这饭就这个吃法。米只炒不焖,在中国人嘴里总归不够火候。遂想起btsb作为爱吃米的中国人在挪威得到的特殊礼遇:沙拉里拌上生大米。
倒是就着啤酒吃的橄榄很不错。有红有绿,参差皴裂,看着象豆子。吃起来也象豆子,软软的,不太咸,嘴一抿吐出核,留下橄榄的清香。一颗不停地吃个精光。
因为不活动胃口不开,早晨吃不下味道太重的东西,所以虽然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老咖啡馆选择众多,一直没找到可心的早点,直到在马拉加吃了清爽的烤面包夹火腿——火腿是咸的但只有薄薄一片,配一碟番茄碎和一包橄榄油,随便搭配。最有趣的是点好后服务员要问你的名字——餐好了,麦克风大叫一声“芭芭拉”,赶紧跳起来去接——在异国他乡陌生餐馆里回荡自己的名字这还是头一遭。于是边吃早点,边自然而然知道了排在我后面的帅哥芳名“雅各布”。



晚餐(巴塞罗那)


午餐(格拉纳达)和早餐(马拉加)
09:45:00 -
bar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