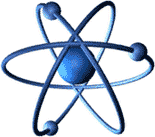Barb的不老歌
28 June
与世界对话
(本观后感献给不在场的f 先生,让他扶着白海棠吐血去吧)
今年看到的最好的舞。
慕尼黑芭团这回唯一一场现代芭蕾,比之前那场雷蒙达好太多了,这才叫真的实力呢。据说他们团经济打理得不错,怀疑古典舞剧是为了保住票房兼政治任务(作为国家团一表泱泱大国之实力),现代舞才是真的苦心孤诣亮剑出鞘,当然好的现代舞都要有好的古典舞作底子。
我要是编舞我也忙不迭把舞拿给他们跳,那么高素质整齐划一的男舞者,高大、强壮、孔武,个个像大卫像。不过遇到这么好的编舞,又谁敢不全力以赴博命演出,诚如与世界对话。
汉斯范曼恩(Hans Van Manen),荷兰舞蹈剧场(NDT)的创建者之一。头三支都是他的舞,温和简洁干净,脱离世俗而耽于世俗,引人不断想靠近再靠近。威廉福赛斯(William Forsythe),这位恐怕是不世出的天才,也难怪以他的舞压大轴,那是一种巨大的把你推开再推开的力量,只能远远凝视,诚惶诚恐,有若膜拜。
一个一个说。
钢琴柔板(Adagio Hammerklavier),七三年荷兰国家芭蕾舞团首演。三对男女舞者双双对对,肃静祥和或分别或共同上场,一对接一对像波涛起伏,前赴后继,再两两相忘。要在很静的境地里,极其专注地落入他们的时空,不霎神,不动情,极静极静。
抄一段节目册上约亨施密特(Jochen Schmidt)的舞评:“它越来越走向沉静和静默、死亡和睡眠;而在那些愉悦的时刻,你的梦境就像范曼恩在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样安逸和欢快……这部作品要求观赏者极度专心、精确观察,它排斥混编节目中一切浅显的引人入胜。这是妙手偶得的一部作品,是范曼恩成就其卓越编舞家的巅峰之作。”
照我看,它并不要求观众极度关心,它几乎是旁若无人地自在开展,是它那股无声的力量像一个梦,伸出无形的手把观众的注意力深深地拉了进去。一切是那么美,规律之美,静谧之美,身体之美。
老人与我(The Old Man and Me),九六年荷兰舞蹈剧场III团首演。这段舞应该是四段舞里最珍贵的,两舞者中朱迪斯杜洛斯(Judith Turos)在零五年就正式荣退,伊凡利斯卡(Ivan Liška)是该团艺术总监,今年五十九岁,头发业已花白,能看到他亲自出马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
节目册上介绍它“是一支介于成熟的忧郁和率直的幽默之间的引人入胜的双人舞”,然也。两位早不年轻的舞者演绎起来驾轻就熟,不讲究技术的锋芒毕露,反倒是无尽的内心戏。轻松的片断引观众发笑了好几次,其中一个互相吹气膨胀,又泄气倒地的段子似曾相识,好象上个月在法国的嘻哈大少(Cie Accrorap)舞团的嘻哈版现代舞《小故事.com》(Petites Histoires.com)里看到过(虽然舞种不同),不知是谁抄谁的。
Judith Turos是看了他们团两场演出我最喜欢的女舞者,她特别有一种技术成熟至圆熟的美感,很放松,精致而优雅,又仍然保留着敏感,像女演员里的Isabelle Huppert。外形到状态上她和老头子很般配,二人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岁月流逝的气场。
这支舞的名字就是一开头节奏轻快的蓝调,J.J. Cale的The Old Man and Me,这种早已淡出大庭广众耳际的曲子在庞大的歌剧院里响起,非常诱惑,像在向庄严肃穆挑战。后面却变成了斯特拉文斯基和莫扎特。莫扎特这段很哀伤,舞蹈没有转成缠绵悱恻,却用了电影剪接的手法:灯灭了又亮,男女相对;灭了再亮,男女侧身;再灭再亮,天涯相望……如此往复、定格,把哀伤处理得简略而干脆。
独自起舞(Solo),九七年荷兰舞蹈剧场II团首演。说是solo,其实有三个人跳,类似第一场钢琴柔板,也是轮流交替上场。汉斯范曼恩的解释是:“我想要使用的巴赫小提琴组曲,单独一位舞者根本不可能演绎出来。”
这场舞火花四溅,噼啪作响,算是比较纯粹的技术秀,有很多快速、危险到华丽的段子,因为太快了太危险了太紧张了,在瞬间戛然而止的时候不免让人拍大腿,怎么这么短啊!
Ivan Liška在演出结束后的交流活动里开玩笑说这段是给观众的巧克力,一点小甜头。我象所有饕餮客一样心想,怎么那么小啊,刚够引起无尽的胃口。
矩阵密云(Enemy in the Figure),八九年法兰克福芭蕾舞团首演。它是威廉福赛斯《身体协奏曲》(Limb's Theorem)的第二部分。我简直要为了它一举爱上他。
这场舞也实在很难形容,冷峻、黑暗、凝结、爆发,周而复始。舞台上同时有多名舞者旋转、跳跃、伸展、行走。一台泛光灯被推着由远及近,在幽深中扫出低浮的微光,一条脉冲白绳像挡路的电线亘结于舞台当中,当你以为他们要被绊倒了,他们却自若地行走在白绳两岸。舞台对角有一波浪形高屏,像舞台的心脏,舞者们翻滚着从中而出,一段展演后又隐匿其后。虽然热闹,每一个倒是踽踽独行的,合着空空作响的大工业电子乐,非常的冷,像未来的机械世界。就连软帅哥Lukáš Slavický也沾染了这股黑色,变得比跳雷蒙达的时候冷硬多了。
矩阵庞大的力量兼幽暗的舞台让我看得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以至进到地铁里的灯光下,小船说我眼睛充血。
Ivan Liška说威廉福赛斯是他所知道的当代编舞家里最富哲学思考的一个,而且涉猎极广又充满了奇思妙想,他用手在池座上划了个圈子说,福赛斯的大脑,有这里的一半那么大。
顺带夸一下翻译dd,长得很斯文,翻译得真是顶呱呱,把Liška的话解释得清楚易懂不说,还把观众的各种无厘头问题翻译得不那么无聊,激发出了一些尚算有价值的八卦(他自己对舞蹈应该很在行)。譬如船看钢琴柔板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巴兰钦,尤其是他的《珠宝》,Liška在回答一个烂问题时就刚好证实了她的感觉。个人觉得他的现场翻译比曹诚渊还好。如果他是大剧院的工作人员,希望以后常常看到他。
其余诸事,音乐、灯光、布景、服装无一不美,用句肉麻的话说就是,连细节也有灵魂。为什么只演一场呢?难道是因为太暴烈强度太大而不能?



今年看到的最好的舞。
慕尼黑芭团这回唯一一场现代芭蕾,比之前那场雷蒙达好太多了,这才叫真的实力呢。据说他们团经济打理得不错,怀疑古典舞剧是为了保住票房兼政治任务(作为国家团一表泱泱大国之实力),现代舞才是真的苦心孤诣亮剑出鞘,当然好的现代舞都要有好的古典舞作底子。
我要是编舞我也忙不迭把舞拿给他们跳,那么高素质整齐划一的男舞者,高大、强壮、孔武,个个像大卫像。不过遇到这么好的编舞,又谁敢不全力以赴博命演出,诚如与世界对话。
汉斯范曼恩(Hans Van Manen),荷兰舞蹈剧场(NDT)的创建者之一。头三支都是他的舞,温和简洁干净,脱离世俗而耽于世俗,引人不断想靠近再靠近。威廉福赛斯(William Forsythe),这位恐怕是不世出的天才,也难怪以他的舞压大轴,那是一种巨大的把你推开再推开的力量,只能远远凝视,诚惶诚恐,有若膜拜。
一个一个说。
钢琴柔板(Adagio Hammerklavier),七三年荷兰国家芭蕾舞团首演。三对男女舞者双双对对,肃静祥和或分别或共同上场,一对接一对像波涛起伏,前赴后继,再两两相忘。要在很静的境地里,极其专注地落入他们的时空,不霎神,不动情,极静极静。
抄一段节目册上约亨施密特(Jochen Schmidt)的舞评:“它越来越走向沉静和静默、死亡和睡眠;而在那些愉悦的时刻,你的梦境就像范曼恩在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样安逸和欢快……这部作品要求观赏者极度专心、精确观察,它排斥混编节目中一切浅显的引人入胜。这是妙手偶得的一部作品,是范曼恩成就其卓越编舞家的巅峰之作。”
照我看,它并不要求观众极度关心,它几乎是旁若无人地自在开展,是它那股无声的力量像一个梦,伸出无形的手把观众的注意力深深地拉了进去。一切是那么美,规律之美,静谧之美,身体之美。
老人与我(The Old Man and Me),九六年荷兰舞蹈剧场III团首演。这段舞应该是四段舞里最珍贵的,两舞者中朱迪斯杜洛斯(Judith Turos)在零五年就正式荣退,伊凡利斯卡(Ivan Liška)是该团艺术总监,今年五十九岁,头发业已花白,能看到他亲自出马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
节目册上介绍它“是一支介于成熟的忧郁和率直的幽默之间的引人入胜的双人舞”,然也。两位早不年轻的舞者演绎起来驾轻就熟,不讲究技术的锋芒毕露,反倒是无尽的内心戏。轻松的片断引观众发笑了好几次,其中一个互相吹气膨胀,又泄气倒地的段子似曾相识,好象上个月在法国的嘻哈大少(Cie Accrorap)舞团的嘻哈版现代舞《小故事.com》(Petites Histoires.com)里看到过(虽然舞种不同),不知是谁抄谁的。
Judith Turos是看了他们团两场演出我最喜欢的女舞者,她特别有一种技术成熟至圆熟的美感,很放松,精致而优雅,又仍然保留着敏感,像女演员里的Isabelle Huppert。外形到状态上她和老头子很般配,二人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岁月流逝的气场。
这支舞的名字就是一开头节奏轻快的蓝调,J.J. Cale的The Old Man and Me,这种早已淡出大庭广众耳际的曲子在庞大的歌剧院里响起,非常诱惑,像在向庄严肃穆挑战。后面却变成了斯特拉文斯基和莫扎特。莫扎特这段很哀伤,舞蹈没有转成缠绵悱恻,却用了电影剪接的手法:灯灭了又亮,男女相对;灭了再亮,男女侧身;再灭再亮,天涯相望……如此往复、定格,把哀伤处理得简略而干脆。
独自起舞(Solo),九七年荷兰舞蹈剧场II团首演。说是solo,其实有三个人跳,类似第一场钢琴柔板,也是轮流交替上场。汉斯范曼恩的解释是:“我想要使用的巴赫小提琴组曲,单独一位舞者根本不可能演绎出来。”
这场舞火花四溅,噼啪作响,算是比较纯粹的技术秀,有很多快速、危险到华丽的段子,因为太快了太危险了太紧张了,在瞬间戛然而止的时候不免让人拍大腿,怎么这么短啊!
Ivan Liška在演出结束后的交流活动里开玩笑说这段是给观众的巧克力,一点小甜头。我象所有饕餮客一样心想,怎么那么小啊,刚够引起无尽的胃口。
矩阵密云(Enemy in the Figure),八九年法兰克福芭蕾舞团首演。它是威廉福赛斯《身体协奏曲》(Limb's Theorem)的第二部分。我简直要为了它一举爱上他。
这场舞也实在很难形容,冷峻、黑暗、凝结、爆发,周而复始。舞台上同时有多名舞者旋转、跳跃、伸展、行走。一台泛光灯被推着由远及近,在幽深中扫出低浮的微光,一条脉冲白绳像挡路的电线亘结于舞台当中,当你以为他们要被绊倒了,他们却自若地行走在白绳两岸。舞台对角有一波浪形高屏,像舞台的心脏,舞者们翻滚着从中而出,一段展演后又隐匿其后。虽然热闹,每一个倒是踽踽独行的,合着空空作响的大工业电子乐,非常的冷,像未来的机械世界。就连软帅哥Lukáš Slavický也沾染了这股黑色,变得比跳雷蒙达的时候冷硬多了。
矩阵庞大的力量兼幽暗的舞台让我看得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以至进到地铁里的灯光下,小船说我眼睛充血。
Ivan Liška说威廉福赛斯是他所知道的当代编舞家里最富哲学思考的一个,而且涉猎极广又充满了奇思妙想,他用手在池座上划了个圈子说,福赛斯的大脑,有这里的一半那么大。
顺带夸一下翻译dd,长得很斯文,翻译得真是顶呱呱,把Liška的话解释得清楚易懂不说,还把观众的各种无厘头问题翻译得不那么无聊,激发出了一些尚算有价值的八卦(他自己对舞蹈应该很在行)。譬如船看钢琴柔板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巴兰钦,尤其是他的《珠宝》,Liška在回答一个烂问题时就刚好证实了她的感觉。个人觉得他的现场翻译比曹诚渊还好。如果他是大剧院的工作人员,希望以后常常看到他。
其余诸事,音乐、灯光、布景、服装无一不美,用句肉麻的话说就是,连细节也有灵魂。为什么只演一场呢?难道是因为太暴烈强度太大而不能?



11:25:07 -
barb -
25 June
雷蒙达
巴伐利亚慕尼黑芭蕾舞团,雷蒙达。
为了去看它,特地套上唯一一条连衣裙,去年I小姐帮我选购的,高胸线没腰(fcuk家的衣服都是这德行不是吗),还蹬上了唯一一对高跟凉鞋。结果午饭时就有好事者问我是不是有状况,我要想了两分钟才明白是什么意思,恼羞成怒。
这还没有够,头天把电源落在另一栋楼,想取了赶班车回到自己办公楼,结果唯一比赶不上班车更悲惨的事情发生了:赶上了班车,但班车没座了。只好跟着一班工程师吭哧吭哧走过去,还要寒暄,还要装作高跟鞋穿得很熟稔的样子。后来发现两只脚对称地磨出了泡。
这仍然没够,下班搭着班车高兴地向目的地挺进,结果发现忘了拿手机,灰溜溜地下车取,灰溜溜地打了个车,灰溜溜地堵车,灰溜溜地绕到长安街后面,在鸟蛋南面下了车,不得不迢迢地绕过池塘走到北门去。这一顿走啊,戾气顿生,恨不得把鞋扒下来扔进他们家水池子里。
总算走到了,找着olimpia,时间也差不多了。饿着肚子找到座位,钟声一响,不由得高兴起来,戾气化为详和。不料到幕一拉开,算开始了——一拨又一拨的人开始入场,黑灯瞎火地在陡峭的台阶上找座位,还有高跟拖鞋敲着地梆梆响。只见我们前排一会儿起一会儿坐,如此热闹了半晌。好不容易静下来了又听见此起彼伏的清嗓子声,这阵仗我看戏都没遇见过。
气归气,努力聚精会神,看进台子上去。他们的灯光很讲究,温柔地变幻,追光追得严丝合缝。布景也讲究,简洁而深,机械师一流,布景有时慢慢移动退下去,悄无声息,真不是戏曲舞台能比的。
谢幕的时候才发现该团资金雄厚,密密麻麻堆满了人,怪堂皇的。他们的男舞者一水儿的高大魁梧型,大概以德国人的精密态度挑拣过,个头宽窄几乎平齐。女舞者不知怎么比较参差,常常双人舞大小个,还一快一慢,看得人难堪。
我是第一次看雷蒙达。话说她是个女伯爵,正在家里开派对。她的未婚夫正准备着十字军东征,送了她一条纱巾作礼物,这时半路来了个程咬金,阿拉伯王子。她一来二去被王子的异国风情迷倒,又收下了他的茉莉花。不知怎么睡着了(芭蕾舞剧里的人物常莫名其妙地睡着不是吗),梦见未婚夫变成了阿拉伯王子。下半场又是一个庆典,雷蒙达再次被阿拉伯王子的男性魅力迷倒,这时未婚夫来了,和王子决斗,一个幽灵般贯穿始终的白衣仙女用神力帮未婚夫刺死了王子。雷蒙达生着生着气,被未婚夫哄了那么几下又好了,结果两人产生了爱情!
这个不靠谱的故事很有点道德训诫的意思,可恨复可笑。可惜我们都喜欢阿拉伯王子胜过未婚夫,理由太充分了,他香艳而短命,像雄版狐狸精,崩解制度、破坏庸常,是万众中的异色,多鹤立鸡群啊。跳他的Alen Bottaini神采奕奕,雄赳赳气昂昂挺胸站着,气场很强。他的动作干脆利落,大跳落地轻如鸿毛,神情倨傲,身体是谦恭的。上半场向美女求爱,迈一步扭两扭,蛇一样的阿拉伯风情,竟然一点也不妖娆,很刚劲呢。
Olimpia因此为雷蒙达的不长眼忿忿不平。
结尾婚礼完了,倒有一段独舞,纱幕后幽蓝光,繁华散尽,美人儿么郁郁寡欢。单看还凑合,安在舞剧里不好,突兀而无解,并不特别地觉得意味深长。
故事瞅着挺热闹的,没想到群舞那么闷(不喜欢这个新版编舞)。我平时最不爱看宫廷舞会,一个挨一个上来轮流献技,感觉像串场,对观众和舞者都不公平,虽然这是正经传统。这回的双人舞上下半场各有一段出彩的地方,头一段是和阿拉伯王子,后一段是和未婚夫。跳未婚夫的Lukáš Slavický身材相貌样样都好,就是动作柔和,落地重,不是我喜欢的那款。
女主角Lisa-Maree Cullum作为他们的头号首席大概很牛,无奈何一开始留意到她的左手,就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好象是个被忽略的部位,一抬手总感觉不是地方,右手和整个身体都没问题,就是觉得那只左手不对劲。不知是我魔障了,还是真是她的宝贵脚后跟。
另一个不舒服的是他们的衣服,设计师该拖出去打,枉费机关算尽的布景了。颜色很不对,第三场的群舞女的穿腌绿裙子,男的穿渐变绿上衣,抱在一起像一堆菜叶子,绿得黯然销魂。舞会上豪华归豪华,衣服往往是撞色,阿拉伯女子们蒙面的蓝纱也很不中看,怪里怪气,一看就是洋人假扮的。比起苏格兰芭团美仑美奂的衣裳,真是差天同地。
总的来说基本没怎么犯困,效果还是挺好的。也多亏中午喝了公司咖啡,小白兔同事说每次喝了以后都心跳手抖神魂颠倒……
星期六有Alen Bottaini的独舞,说什么也要弄张黄牛票去看。
为了去看它,特地套上唯一一条连衣裙,去年I小姐帮我选购的,高胸线没腰(fcuk家的衣服都是这德行不是吗),还蹬上了唯一一对高跟凉鞋。结果午饭时就有好事者问我是不是有状况,我要想了两分钟才明白是什么意思,恼羞成怒。
这还没有够,头天把电源落在另一栋楼,想取了赶班车回到自己办公楼,结果唯一比赶不上班车更悲惨的事情发生了:赶上了班车,但班车没座了。只好跟着一班工程师吭哧吭哧走过去,还要寒暄,还要装作高跟鞋穿得很熟稔的样子。后来发现两只脚对称地磨出了泡。
这仍然没够,下班搭着班车高兴地向目的地挺进,结果发现忘了拿手机,灰溜溜地下车取,灰溜溜地打了个车,灰溜溜地堵车,灰溜溜地绕到长安街后面,在鸟蛋南面下了车,不得不迢迢地绕过池塘走到北门去。这一顿走啊,戾气顿生,恨不得把鞋扒下来扔进他们家水池子里。
总算走到了,找着olimpia,时间也差不多了。饿着肚子找到座位,钟声一响,不由得高兴起来,戾气化为详和。不料到幕一拉开,算开始了——一拨又一拨的人开始入场,黑灯瞎火地在陡峭的台阶上找座位,还有高跟拖鞋敲着地梆梆响。只见我们前排一会儿起一会儿坐,如此热闹了半晌。好不容易静下来了又听见此起彼伏的清嗓子声,这阵仗我看戏都没遇见过。
气归气,努力聚精会神,看进台子上去。他们的灯光很讲究,温柔地变幻,追光追得严丝合缝。布景也讲究,简洁而深,机械师一流,布景有时慢慢移动退下去,悄无声息,真不是戏曲舞台能比的。
谢幕的时候才发现该团资金雄厚,密密麻麻堆满了人,怪堂皇的。他们的男舞者一水儿的高大魁梧型,大概以德国人的精密态度挑拣过,个头宽窄几乎平齐。女舞者不知怎么比较参差,常常双人舞大小个,还一快一慢,看得人难堪。
我是第一次看雷蒙达。话说她是个女伯爵,正在家里开派对。她的未婚夫正准备着十字军东征,送了她一条纱巾作礼物,这时半路来了个程咬金,阿拉伯王子。她一来二去被王子的异国风情迷倒,又收下了他的茉莉花。不知怎么睡着了(芭蕾舞剧里的人物常莫名其妙地睡着不是吗),梦见未婚夫变成了阿拉伯王子。下半场又是一个庆典,雷蒙达再次被阿拉伯王子的男性魅力迷倒,这时未婚夫来了,和王子决斗,一个幽灵般贯穿始终的白衣仙女用神力帮未婚夫刺死了王子。雷蒙达生着生着气,被未婚夫哄了那么几下又好了,结果两人产生了爱情!
这个不靠谱的故事很有点道德训诫的意思,可恨复可笑。可惜我们都喜欢阿拉伯王子胜过未婚夫,理由太充分了,他香艳而短命,像雄版狐狸精,崩解制度、破坏庸常,是万众中的异色,多鹤立鸡群啊。跳他的Alen Bottaini神采奕奕,雄赳赳气昂昂挺胸站着,气场很强。他的动作干脆利落,大跳落地轻如鸿毛,神情倨傲,身体是谦恭的。上半场向美女求爱,迈一步扭两扭,蛇一样的阿拉伯风情,竟然一点也不妖娆,很刚劲呢。
Olimpia因此为雷蒙达的不长眼忿忿不平。
结尾婚礼完了,倒有一段独舞,纱幕后幽蓝光,繁华散尽,美人儿么郁郁寡欢。单看还凑合,安在舞剧里不好,突兀而无解,并不特别地觉得意味深长。
故事瞅着挺热闹的,没想到群舞那么闷(不喜欢这个新版编舞)。我平时最不爱看宫廷舞会,一个挨一个上来轮流献技,感觉像串场,对观众和舞者都不公平,虽然这是正经传统。这回的双人舞上下半场各有一段出彩的地方,头一段是和阿拉伯王子,后一段是和未婚夫。跳未婚夫的Lukáš Slavický身材相貌样样都好,就是动作柔和,落地重,不是我喜欢的那款。
女主角Lisa-Maree Cullum作为他们的头号首席大概很牛,无奈何一开始留意到她的左手,就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好象是个被忽略的部位,一抬手总感觉不是地方,右手和整个身体都没问题,就是觉得那只左手不对劲。不知是我魔障了,还是真是她的宝贵脚后跟。
另一个不舒服的是他们的衣服,设计师该拖出去打,枉费机关算尽的布景了。颜色很不对,第三场的群舞女的穿腌绿裙子,男的穿渐变绿上衣,抱在一起像一堆菜叶子,绿得黯然销魂。舞会上豪华归豪华,衣服往往是撞色,阿拉伯女子们蒙面的蓝纱也很不中看,怪里怪气,一看就是洋人假扮的。比起苏格兰芭团美仑美奂的衣裳,真是差天同地。
总的来说基本没怎么犯困,效果还是挺好的。也多亏中午喝了公司咖啡,小白兔同事说每次喝了以后都心跳手抖神魂颠倒……
星期六有Alen Bottaini的独舞,说什么也要弄张黄牛票去看。
21:28:20 -
barb -
02 June
卡门阵容

苏格兰芭蕾舞团卡门阵容:
卡门:Martina Forioso (出生地意大利都灵)
斗牛士:William Smith(出生地美国弗吉尼亚)
荷西:Daniel Davidson (出生地英国爱丁堡)
老头儿是英国文化官员。
22:42:36 -
barb -
01 June
老牛嫩草之夜②
卡门之后,喜从天降(Pennies from Heaven),编舞是艺术总监阿什利佩吉(Ashley Page),八十年代是英国皇家芭蕾舞团主演。我总怀疑他管理的能力要比编舞强,看苏格兰芭蕾舞团那有意的娇嫩欲滴不脱清涩的舞者们,又是形形色色不分国界,两者都有刻意的嫌疑,而且功夫没撂下,在《喜从天降》里各显神通,像一场舞林大会。
据说原作是八十年代初的同名电视剧(编剧Dennis Potter)。
背景是座吧台,墙上贴着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的巨幅照片,音乐无不三十年代。吧台里外,人来人往,一时是门童和侍女,一时是绅士和艳妇,一时是邻家客,一时是远行人……一会儿酒保在摇酒壶,一会儿老情人倚着吧台再干一杯。
来来往往的一对对各怀奇技,有时双人舞,有时是群舞,蹬蹬跺地,就还原了一个时代。服装很漂亮,尤其一袭翠绿色夜礼服裙子,配着舞者的红头发……可以媲美《赎罪》(Atonement)里凯拉奈特利用来拗造型那袭。
他们的舞者就是各出奇军,新西兰、法国、意大利、芬兰、俄罗斯、美国、马耳他、西班牙、阿根廷、日本、韩国……简直没有重样儿的。有一个日本mm面容甜美,像个大了一号的I小姐:P
人、舞、衣服、音乐,样样都没落下,然而怎么都觉得不对劲。散场时坐我隔壁偶然认识的MD小姐(是真医生哦)说,太多重复,没完没了……回到家看电视上放《甜姐儿》(Funny Face)我才突然想起来哪儿不对:那是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的时代,舞王岂可复制。
21:42:36 -
bar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