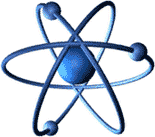Barb的不老歌
31 May
巴登巴登
前几天和振平躲在会议室里瞎聊天,讨论起假期计划(六月二至六日放假五天,庆祝耶稣升天),他说起要重游巴登巴登,说得我开始怀念那儿的澡堂子。上次去斯图加特找Joy看芭蕾,一道去了巴登巴登,在腓特烈(Friedrich)温泉浴场泡了几个钟头,历经大大小小十三个步骤,又蒸又淋又泡,让不谙水性的我饱尝水汽。美中不足的是后来历时一个月之久的咳嗽初露端倪,我怕被人鄙视匆匆逃离,忽略了最后一步的大圆池————男女同浴处。倒不是多么渴望见到裸男,反正我这大近视什么也看不清,只是想看看开阔的高圆顶,和左右两翼(一边是男一边是女,分别历经前面十三道工序)会师的情景。泡完澡,浑身的力气(和戾气)都泡光了,回程路上,都是Joy一个人辛辛苦苦开车,我努力想尽到副驾的职责——和司机聊天防止瞌睡,可是不争气地自己先昏睡过去。后来遗憾地想,但凡我当时体力好一点,两个人在水池子里再多聊聊天多好,去高温蒸汽室多蒸一会儿欣赏一下花枝与鸟的瓷砖多好。这个澡堂子有百年历史,和另一家较摩登的一比较,Joy当机立断:当然是去老的。
巴登巴登离斯图加特远,离法兰克福近。我之所以想起走这么一遭,首先是因为俄国人的一本小说,其次是fuge的“强行除衫记”推波助澜。
俄国人叫列昂尼德·茨普金,小说叫《巴登夏日》。听名字还以为是夏日烟云般的爱情故事,没想到是一本偶像崇拜记,一个平生从未发表过作品的文学爱好者对自己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敬礼。像传记又不是传记,因为有作者的身影贯穿始终,像小说又不是小说,因为全是依据陀太太的笔记。读起来嘛也不算好读,段落长又充满了个人化的呓语,我之所以读下去完全是因为感叹于作者的特殊经历(读另一本不知所云的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也是好奇于作者多过小说的吸引力)。
苏珊·桑塔格的序言是这么介绍的:
茨普金活了五十六岁,一九八二年去世。之前是前苏联的一个普通医学研究员。家人有的遭政治迫害,有的被德国人杀害,战争结束后他沿袭父业开始做医生。他一生爱好文学和电影,但在政治环境和家庭负担两重压力下一直没时间搞创作,直到四十四岁开始在生命的最后十一年写出几部小说——没有一点发表的希望,家里仅有的从事文艺的人,他的姨妈毫不留情地打击他的作品。一九七七年他的儿子儿媳决定申请去美国,人一走,这位老爹就被降职(之前太太已经辞去工作,因为怕美国签证官对儿子儿媳有偏见),工资砍掉百分之七十五,也不可能另谋生路,因为有儿子移民美国的“污点”。夫妇俩申请了两次移民美国,等待了几年时间,被告知“永远不会获准”。《巴登夏日》在国内出版不可能,他冒险托记者朋友把手稿带出苏联。他儿子才帮他投稿成功,连载在一份纽约发行的俄罗斯移民报上,他就心脏病突发死掉了。
这本书神奇的地方有两个:第一,茨普金是犹太人,他这位超级偶像,一向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是反犹的,于是他越迷恋越不解越痛苦。第二,这本几乎无声消逝的小说一旦被苏珊·桑塔格发现,并猛赞为“把俄罗斯文学中所有伟大的主题都表现了出来”,“如果想读一本书就能体验到俄罗斯文学的深刻与力量,就读这本书吧”,立刻成了“文学史上被遗忘的十大杰作之一”。
因为基本没读过俄罗斯小说,无法苟同桑塔格,但是的确在这本小说里读到了作者的高度敏感和无声深处的痛苦,他可真是个生活在时代和命运夹角里的人,肯定还不是唯一的一个。小说里没有美化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跑到巴登巴登去不是为了泡温泉,而是为了赌钱——艺术世界的高远和创作者的现实生活差天同地,奇就奇在作者对他没有任何评价,几乎是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咂摸他的踪迹和行为,这么深切的迷恋和悲伤!与其说这是读一本文学奇迹,还不如说是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猎奇。我和Joy还专门跑到小城赌场兜了一圈,没开门,但从外头怎么也看不出它是怎么成为旧欧洲的赌博中心的,曾经扑腾在门里门外的名人显贵一点踪影也没留下。


赌场

澡堂
巴登巴登离斯图加特远,离法兰克福近。我之所以想起走这么一遭,首先是因为俄国人的一本小说,其次是fuge的“强行除衫记”推波助澜。
俄国人叫列昂尼德·茨普金,小说叫《巴登夏日》。听名字还以为是夏日烟云般的爱情故事,没想到是一本偶像崇拜记,一个平生从未发表过作品的文学爱好者对自己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敬礼。像传记又不是传记,因为有作者的身影贯穿始终,像小说又不是小说,因为全是依据陀太太的笔记。读起来嘛也不算好读,段落长又充满了个人化的呓语,我之所以读下去完全是因为感叹于作者的特殊经历(读另一本不知所云的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也是好奇于作者多过小说的吸引力)。
苏珊·桑塔格的序言是这么介绍的:
茨普金活了五十六岁,一九八二年去世。之前是前苏联的一个普通医学研究员。家人有的遭政治迫害,有的被德国人杀害,战争结束后他沿袭父业开始做医生。他一生爱好文学和电影,但在政治环境和家庭负担两重压力下一直没时间搞创作,直到四十四岁开始在生命的最后十一年写出几部小说——没有一点发表的希望,家里仅有的从事文艺的人,他的姨妈毫不留情地打击他的作品。一九七七年他的儿子儿媳决定申请去美国,人一走,这位老爹就被降职(之前太太已经辞去工作,因为怕美国签证官对儿子儿媳有偏见),工资砍掉百分之七十五,也不可能另谋生路,因为有儿子移民美国的“污点”。夫妇俩申请了两次移民美国,等待了几年时间,被告知“永远不会获准”。《巴登夏日》在国内出版不可能,他冒险托记者朋友把手稿带出苏联。他儿子才帮他投稿成功,连载在一份纽约发行的俄罗斯移民报上,他就心脏病突发死掉了。
这本书神奇的地方有两个:第一,茨普金是犹太人,他这位超级偶像,一向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是反犹的,于是他越迷恋越不解越痛苦。第二,这本几乎无声消逝的小说一旦被苏珊·桑塔格发现,并猛赞为“把俄罗斯文学中所有伟大的主题都表现了出来”,“如果想读一本书就能体验到俄罗斯文学的深刻与力量,就读这本书吧”,立刻成了“文学史上被遗忘的十大杰作之一”。
因为基本没读过俄罗斯小说,无法苟同桑塔格,但是的确在这本小说里读到了作者的高度敏感和无声深处的痛苦,他可真是个生活在时代和命运夹角里的人,肯定还不是唯一的一个。小说里没有美化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跑到巴登巴登去不是为了泡温泉,而是为了赌钱——艺术世界的高远和创作者的现实生活差天同地,奇就奇在作者对他没有任何评价,几乎是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咂摸他的踪迹和行为,这么深切的迷恋和悲伤!与其说这是读一本文学奇迹,还不如说是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猎奇。我和Joy还专门跑到小城赌场兜了一圈,没开门,但从外头怎么也看不出它是怎么成为旧欧洲的赌博中心的,曾经扑腾在门里门外的名人显贵一点踪影也没留下。


赌场

澡堂
20:53:37 -
barb -
29 May
三体
前几天夜里睡不着,开始看刘慈欣的《三体》,一下就被勾住了。刚开始看还有点恐怖,看到宇宙为一个人而闪烁,不由毛骨悚然,看到后半部分才感到欣慰,原来没走到惊悚玄幻的路子上呀,还是科幻小说。第一部看完印证了刚开始看时的感觉,这小说和Stieg Larsson的《龙纹身的女孩》(The Girl with a Dragon Tattoo)太象了,不是内容,而是类型元素的杂烩。小说的主线是科幻,却有伤痕、惊悚、探险(比如盗墓小说)、政治、历史、心理分析、网游……等等类型小说的痕迹,而一路解谜的过程,根本就是侦探小说嘛(还真有个不招人待见的粗鲁警官大史)。我感到最满意的是,每次对某个情节发展的逻辑有所置疑时,后来总会有人物跳出来把它说圆了————科幻小说的本质是小说,小说的本质是讲故事不是吗(我反对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虽然对里头涉及的物理、天文、计算机理论没啥头绪,但不影响阅读,我很满意。
八十年代,据说国内有一个科幻小说写作的高潮,我无知无觉。但当时的确看过不知从哪儿流来的翻译科幻小说,大多是机器人和外星人题材,没有阿西莫夫高级,情节走向一半一半,不是把他们写作邪恶不可控的力量,就是把他们写成拯救地球的天外飞仙。刘作者的好处是试图想像他们最可能的面貌(只是试图),这就让编的故事显得比较不傻。他还有点小小的幽默感,偶尔拿网络语言搞搞笑,或者写一笔明显是他心仪的福尔摩斯什么的,让人感觉很亲切。
C某顺手查了一下他的背景,我看到他现在工作于娘子关火电站,问道“这个电站为啥叫娘子关火啊?”某人……是啊,象我这样儿的老无知竟然也读科幻小说。现在开始看第二部《黑暗森林》,谢谢皮皮和I小姐友情分享。
八十年代,据说国内有一个科幻小说写作的高潮,我无知无觉。但当时的确看过不知从哪儿流来的翻译科幻小说,大多是机器人和外星人题材,没有阿西莫夫高级,情节走向一半一半,不是把他们写作邪恶不可控的力量,就是把他们写成拯救地球的天外飞仙。刘作者的好处是试图想像他们最可能的面貌(只是试图),这就让编的故事显得比较不傻。他还有点小小的幽默感,偶尔拿网络语言搞搞笑,或者写一笔明显是他心仪的福尔摩斯什么的,让人感觉很亲切。
C某顺手查了一下他的背景,我看到他现在工作于娘子关火电站,问道“这个电站为啥叫娘子关火啊?”某人……是啊,象我这样儿的老无知竟然也读科幻小说。现在开始看第二部《黑暗森林》,谢谢皮皮和I小姐友情分享。
18:30:18 -
barb -
23 May
面试
为期近半年的面试因故中断,俺只好停止扑腾,老老实实在瑞典呆下去。不过这些面试很给无聊的冬季生活添姿添彩,回想起来还挺有趣——和地球某一隅的某个人通过一根电话线交流,试探、揣测、吸引,象舞步一样你踏前来他退后,逐个试验,直到互相觅得Mr. Right。这种体验恋爱、购物都能提供,不过前者耗时费力,后者缺乏人气,都不如面试性价比高,娱乐性强。
谈过的人里,有在新加坡工作的奥地利人、在布鲁塞尔工作的荷兰人、在香港工作的马来西亚人、在北京工作的法国人、在深圳工作的印度人……态度卑亢各异,口音五花八门。最拽的一位由秘书接通电话,以一种垂帘听政的口吻问,你叫啥来着?又一位北京胡同口音的资深副总裁上来就侃价,你看就我们这职位,你能不能给个实价,说说最低要多少?最失败的是印度大哥,说了半小时,他说的话我连蒙带猜听懂一半,事后沮丧地向Junshan讨教经验,她安慰我,不是你的问题,去印度出差,口音最轻的也只能听懂百分之七十五。
也有好玩的。跟一位首席运营官通电话,说着说着,他说哎呀,好像说是地震了。我说那您快跑吧,他说没事儿,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咱们接着聊。放下电话,扭开电视,CNN正播报一小时前日本地震,海啸黑压压吞噬楼房。过了一会儿猎头来电,警报解除,头儿们从地面跑回来了,下一位继续。
因为我所从事的职业,大多数在矩阵结构里工作,工作关系错综复杂,八杆子打不着的reference面试就少不了。因为多半不是本职能部门的人,问题非常广泛,更多是刺探价值观和软技能。于是收到一些一时半会儿被砸得发懵的问题,这些问题固然没有黑白对错的标准答案,倒也颇具赌博色彩,全看你和出题人是不是臭味相投。我一般的办法就是实话实说,等着王八绿豆看对眼。譬如有一个以前提过的问题,“你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呃,我的感觉就还挺隐私的,于是避结论而取过程,答她“求仁得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最重要,追求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就是幸福,不知道想要什么一切无从谈起”。又一个问题问,“你平生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顾左而言他,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就拣个最近的说吧……”立刻被这位精明的仁兄打断,说“不要最近的,说最大的。”好吧,这哪里是面试,这是逼着人直面惨淡的人生。还被某传统行业问过“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管理者?”问得我一呆,我什么时候变成管理者了?
跟欧洲人面试最舒服,因为很容易就聊到跨文化,最后结束于共同谴责瑞典的社会主义大锅饭。跟香港人聊就比较直接,开门见山到措手不及。在罗马的时候和猎头小姐谈价钱,她操着流利的港式普通话说,拿,他们这个package我都不觉得高,但就是一句话,你要不要进这一行,IT早就穷途末路啦,这个是朝阳行业,你进去两年再跳不好哇。跟英国人聊,就是刚开始彬彬有礼,婉转得你不知道他说啥,偶尔碰上个他的兴趣点,一下八卦劲儿就上来了,追着我问那么伦德跑到马尔默坐公车只要半小时?啥,十三分?挖,那么俺去伦德挖人也可以啦?碰到说中文的呢,我还是后来才意识到自己超乎寻常的兴奋,非常话痨(总算找着聊天的了,说什么不要紧),对方估计被我突然爆发的热情搞得莫名其妙。
总而言之,面试真是人生一面镜子,从别人眼里观照自己,是个有意思的准社会化过程,娱人娱己。
谈过的人里,有在新加坡工作的奥地利人、在布鲁塞尔工作的荷兰人、在香港工作的马来西亚人、在北京工作的法国人、在深圳工作的印度人……态度卑亢各异,口音五花八门。最拽的一位由秘书接通电话,以一种垂帘听政的口吻问,你叫啥来着?又一位北京胡同口音的资深副总裁上来就侃价,你看就我们这职位,你能不能给个实价,说说最低要多少?最失败的是印度大哥,说了半小时,他说的话我连蒙带猜听懂一半,事后沮丧地向Junshan讨教经验,她安慰我,不是你的问题,去印度出差,口音最轻的也只能听懂百分之七十五。
也有好玩的。跟一位首席运营官通电话,说着说着,他说哎呀,好像说是地震了。我说那您快跑吧,他说没事儿,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咱们接着聊。放下电话,扭开电视,CNN正播报一小时前日本地震,海啸黑压压吞噬楼房。过了一会儿猎头来电,警报解除,头儿们从地面跑回来了,下一位继续。
因为我所从事的职业,大多数在矩阵结构里工作,工作关系错综复杂,八杆子打不着的reference面试就少不了。因为多半不是本职能部门的人,问题非常广泛,更多是刺探价值观和软技能。于是收到一些一时半会儿被砸得发懵的问题,这些问题固然没有黑白对错的标准答案,倒也颇具赌博色彩,全看你和出题人是不是臭味相投。我一般的办法就是实话实说,等着王八绿豆看对眼。譬如有一个以前提过的问题,“你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呃,我的感觉就还挺隐私的,于是避结论而取过程,答她“求仁得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最重要,追求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就是幸福,不知道想要什么一切无从谈起”。又一个问题问,“你平生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顾左而言他,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就拣个最近的说吧……”立刻被这位精明的仁兄打断,说“不要最近的,说最大的。”好吧,这哪里是面试,这是逼着人直面惨淡的人生。还被某传统行业问过“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管理者?”问得我一呆,我什么时候变成管理者了?
跟欧洲人面试最舒服,因为很容易就聊到跨文化,最后结束于共同谴责瑞典的社会主义大锅饭。跟香港人聊就比较直接,开门见山到措手不及。在罗马的时候和猎头小姐谈价钱,她操着流利的港式普通话说,拿,他们这个package我都不觉得高,但就是一句话,你要不要进这一行,IT早就穷途末路啦,这个是朝阳行业,你进去两年再跳不好哇。跟英国人聊,就是刚开始彬彬有礼,婉转得你不知道他说啥,偶尔碰上个他的兴趣点,一下八卦劲儿就上来了,追着我问那么伦德跑到马尔默坐公车只要半小时?啥,十三分?挖,那么俺去伦德挖人也可以啦?碰到说中文的呢,我还是后来才意识到自己超乎寻常的兴奋,非常话痨(总算找着聊天的了,说什么不要紧),对方估计被我突然爆发的热情搞得莫名其妙。
总而言之,面试真是人生一面镜子,从别人眼里观照自己,是个有意思的准社会化过程,娱人娱己。
21:03:55 -
barb -
09 May
路易斯安那
从去年春天就一直听到人说丹麦的路易斯安那(Louisiana)现代美术馆,因为说近不近,说远不远,拖到最近才去。从马尔默坐火车到哥本哈根(半小时),再往南接着坐半小时,到一个叫Humlebæk的小镇子再走上一两里路就到了。Humlebæk号称阿姆雷特的家,如果他真的活在这世上的话。
美术馆的入口不大,也就像个乡绅的家,进去以后不得了,是森林草地大海围起来的广阔天地,携家带口野游的人不少。展厅是长廊式的平房,全落地玻璃窗,在室内也感觉海阔天空。现在的特展是毕加索,大家听说都摇摇头,对这位多产的老先生十分麻木。但是丹麦人的布展比西班牙人高明许多,布局、灯光乃至介绍都比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生动。
常规展览比较普通(我总的来说对当代艺术无感),不见得比丹麦国立美术馆好,不过有一幅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安迪沃霍的丝网印刷,还有一幅我更感兴趣的Roy Lichtenstein。更难忘的展览其实是英国画家David Hockney的iPad画巡展,这位老兄画油画中规中矩,一旦移师电子画布顿时风生水起,什么日常什物都能入画,透着电子显示器的荧光,说不出的生动明媚,他老人家还常常边画拿iPhone发给朋友们——看了看展览赞助商,竟然不是苹果,而是YSL。
比艺术更有口碑的恐怕是他们的餐厅,号称咖啡店,实际上像个露天大饭店,门外的人比门里多,就着日光享用午饭。菜式很简单,早午餐和三明治。我们选了时令的熏三文鱼和牛肉,不得不说,虽然只有一海之隔,丹麦人的调味水平比瑞典人高明很多,“健康”得不行的七谷三明治也很开胃。吃饱肚子就在辽阔的院子里溜达,看一会儿玉兰花,摸摸雕像,打个盹儿,再去商店买两件丹麦设计小玩意儿,一天就消耗掉了。

Roy Lichtenstein也毕加索化了……

Andy Warhol



院儿里晒太阳

餐厅外

美术馆的入口不大,也就像个乡绅的家,进去以后不得了,是森林草地大海围起来的广阔天地,携家带口野游的人不少。展厅是长廊式的平房,全落地玻璃窗,在室内也感觉海阔天空。现在的特展是毕加索,大家听说都摇摇头,对这位多产的老先生十分麻木。但是丹麦人的布展比西班牙人高明许多,布局、灯光乃至介绍都比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生动。
常规展览比较普通(我总的来说对当代艺术无感),不见得比丹麦国立美术馆好,不过有一幅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安迪沃霍的丝网印刷,还有一幅我更感兴趣的Roy Lichtenstein。更难忘的展览其实是英国画家David Hockney的iPad画巡展,这位老兄画油画中规中矩,一旦移师电子画布顿时风生水起,什么日常什物都能入画,透着电子显示器的荧光,说不出的生动明媚,他老人家还常常边画拿iPhone发给朋友们——看了看展览赞助商,竟然不是苹果,而是YSL。
比艺术更有口碑的恐怕是他们的餐厅,号称咖啡店,实际上像个露天大饭店,门外的人比门里多,就着日光享用午饭。菜式很简单,早午餐和三明治。我们选了时令的熏三文鱼和牛肉,不得不说,虽然只有一海之隔,丹麦人的调味水平比瑞典人高明很多,“健康”得不行的七谷三明治也很开胃。吃饱肚子就在辽阔的院子里溜达,看一会儿玉兰花,摸摸雕像,打个盹儿,再去商店买两件丹麦设计小玩意儿,一天就消耗掉了。

Roy Lichtenstein也毕加索化了……

Andy Warhol



院儿里晒太阳

餐厅外

20:33:05 -
barb -
01 May
韩国饭
自从上回来我们家吃饭后,振平看见我就要说,我们在准备请你们吃饭哦。鉴于知道七濑压根儿不会做饭,我每次就微笑地听一听,跟他说,不急不急。架不住日本人有恩必报不能欠别人的文化,还是收到了邀请。我满心以为要吃一顿日本饭,想着不知道是吃咖喱还是煎饺,没想到吃了一顿韩国饭。一则七濑的家冲绳和日本本土文化差异很大,二则她在阿拉斯加和汉城留过学,成年的过程一半在海外,三则韩国饭材料大概好找一些。正好前阵子Jun表扬的石锅拌饭让我流了半天口水,这下吃上了。
在北京吃惯的宗家府泡菜竟然让他们在马尔默找着了,本城韩国人超过二十个就了不起了,亚洲商店买的泡菜于是甜腻腻的很不地道。我一直怀念传统韩国泡菜里那股发酵的刺激味……见过的韩国人里除了I小姐从前的博士室友都没什么好印象,对韩国饭的印象倒很好。北京住处附近和公司所在地是两大韩国人聚居区,因此平日没少下韩国馆子。非常喜欢萨拉伯尔的辣萝卜,香猪坊的葱饼(千万别吃五道口的),望京一家韩国汤店的大酱汤和炒米条,另一家二楼韩国店的干白菜辣猪脊骨锅——在冬天轻易打败各路菜系,成为我们组午餐的最爱。还有一家朝鲜馆子海棠花,比韩国菜传统,象小时候鲜族同学家里做饭的风味,石锅饭以他们家最美味,人高马大的漂亮服务员胸前别着“金日成同志”的像章,一直是我们八卦的对象。
我给饭菜拍照,七濑因为是第一次在家请客,高兴得连声道谢。食物清爽美味,振平和C同学喝得酒酣头热。我还借机拍了他们婚礼上摆的小熊——七濑的妈妈亲手做的,和新人们日常的样子很相似。


鸡蛋的做法是,煮熟剖开,把蛋黄挖出来和切碎的辣白菜拌在一起再放回蛋青托子里。


拌饭和杂菜粉丝。后者的秘诀是红薯粉。

冲绳土产,三十度。

在北京吃惯的宗家府泡菜竟然让他们在马尔默找着了,本城韩国人超过二十个就了不起了,亚洲商店买的泡菜于是甜腻腻的很不地道。我一直怀念传统韩国泡菜里那股发酵的刺激味……见过的韩国人里除了I小姐从前的博士室友都没什么好印象,对韩国饭的印象倒很好。北京住处附近和公司所在地是两大韩国人聚居区,因此平日没少下韩国馆子。非常喜欢萨拉伯尔的辣萝卜,香猪坊的葱饼(千万别吃五道口的),望京一家韩国汤店的大酱汤和炒米条,另一家二楼韩国店的干白菜辣猪脊骨锅——在冬天轻易打败各路菜系,成为我们组午餐的最爱。还有一家朝鲜馆子海棠花,比韩国菜传统,象小时候鲜族同学家里做饭的风味,石锅饭以他们家最美味,人高马大的漂亮服务员胸前别着“金日成同志”的像章,一直是我们八卦的对象。
我给饭菜拍照,七濑因为是第一次在家请客,高兴得连声道谢。食物清爽美味,振平和C同学喝得酒酣头热。我还借机拍了他们婚礼上摆的小熊——七濑的妈妈亲手做的,和新人们日常的样子很相似。


鸡蛋的做法是,煮熟剖开,把蛋黄挖出来和切碎的辣白菜拌在一起再放回蛋青托子里。


拌饭和杂菜粉丝。后者的秘诀是红薯粉。

冲绳土产,三十度。

10:51:51 -
bar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