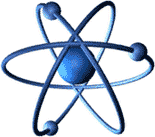Barb的不老歌
15 March
激情、热情和傻笑
昨天我从当当网上订的书和碟到货了,其中有一本《CD流浪记》又脏又破,夹在茨威格、福斯特、菲茨杰拉德什么的书之间一点也不显眼,价钱也便宜,打了好几折,再加上是个我没听说过的作者,所以基本没放在心上。
订购这书的时候也有点偶然性,是看到了网上一位购买者的大力推荐,他说这书比同系列的李欧梵什么的写的要好多了。李欧梵那本我看过,觉得写的还可以,所以即便这书只有这么一条孤伶伶的推荐,我还是看在眼里,被牵动了购物神经。
回家时在班车上开始看,先看了第一篇,就是《CD流浪记》,写作者得了意外一笔稿费还是什么的钱,立刻就跑到台北去买CD,从白天买到天黑,逛遍了大小唱片店,在尘埃里把自己早看上的CD搬回家去,回家时风尘仆仆,抗着装满CD的大袋子,既没钱打车又没钱买烟,打电话让老婆骑摩托车接了回去的。我心想,妈妈咪呀,有这么个老公可真够倒霉的。
晚上回到家,因为先试了《费城》的电影原声CD,等着洗衣机洗衣服之余,又看了会努瑞耶夫和玛歌芳婷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把这本不起眼的书扔在了一边儿。直到今天早晨又拿起来。结果一下被吸引住了,简直着了迷。
我看的时候又翻回头看书的作者吕正惠的名字,以前确实没听说过,看他的描述好象是在大学里任教职的,是台湾人。我真该早点认识他呀,就像他那篇《贝多芬,你在想什么?》,他又崇拜又亲近地和贝多芬对话,称他为“你”。
先被震撼了一下的,是他写他的最爱的那篇,《我喜欢海顿》。就像他的标题一样,他表示对一个偶像的无边敬意时,也是很简洁和朴素的,完全不像我这个感情派,老是在某一分钟狂喜得直跳脚,没头没脑的像个花痴。
说到这儿想起来一小截昨天和Cathayan在MSN上的讨论。话题是从他先做了,后来我又要来做的心理测试上起来的。那个测试的主题是看你的性格有多少男性的成分和多少女性的成分,和一切无聊的性格测试一样,把爱读non-fiction、倾向于倾向而不是发表意见……的特征都归入女性范畴,所以Cathayan和我和大多数人,都得了女性气质的毛病。Cathayan当然一笑置之,我却很懊恼,因为老以为我是有些男性气质的。我跟Cathayan说,我是感情派,我期望我自己70%是感情,30%是理智,Cathayan说,应该是反过来才对啊!我说为什么,你们那么理智的,根本体会不到激情、热情和狂喜,Cathayan说,在理智的基础上一样可以有激情、热情和傻笑,而且可以体会得更深刻(我还问他我目前是怎么样的比例,他说是50%对50%)。
随着近半年对各种乱七八糟东西的心得和体会,我不得不承认,他这话是对的。
而看这本《CD流浪记》,我立刻更深地体会到了这点,而且,我感觉到,这位吕正惠的行文、口吻、表达感情的方式和内在的那种宽阔的包容力,不偏不倚,正是我所追求和期盼看到的那种。
我对古典音乐,别说是欣赏者,连入门都谈不到,而且一直是从Wilde、《魂断威尼斯》、Ferrinelli那些电影里汲取断简残章,直到去年才听了第一场完整的现场音乐会。但是好象随着对舞蹈的喜爱,对音乐的渴求也越来越多,虽然没有刻意地买CD(我买的影碟已经够多的了,实在负担不了),但电视遥控器的常用键除了几个电影和播历史频道节目的频道以外,也常常被按到以古典音乐为主的音乐台。
以前听音乐时,最大的感受莫过于,电影、绘画、小说戏剧和舞蹈这几样,都太倚重于欣赏者个人的经历,搀杂了很多后天的东西,比如所受的教育、知识、价值观……等等,而音乐是直指人心的,更偏重于人先天的性格。我听过一首海顿的交响乐,就完全不喜欢,一点说不上原因。
现在看了吕正惠说海顿的这篇,我才明白,首先音乐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当然仍然要听凭自己从自己内心里去欣赏,而不是去听评论家的),其次,我之所以不喜欢海顿,可能就是太片面化太简单化,或者说太感情化地得出自己的结论了。当然,可能把海顿买齐了,买来各种版本,我也可能仍然不喜欢他,但那时,或者有可能得出建筑在理性之上的感情了。
所以,我觉得吕正惠的这本小书,最让我着迷的就是,他自己有一个宽阔的心胸,并在字里行间使得别人也变得心胸开阔,可以敞开胸襟去看这个音乐的世界,把自己变得很少,美妙的世界就变大了。
另外,对于我,这本书真是最好的入门指南,因为他可以容纳的空间很大,所以他谈论的范围普遍到了几乎所有最著名的作曲家,还有我也越来越感兴趣的歌剧。同时,由于他那成千上万的CD,常常是每晚3数小时的聆听,对音乐家作品的熟悉和对音乐家生活背景的熟悉,和广播的同情心、理解力,常常让我这个阅读者散发同样的感慨。我并不急于马上按着他的指引去买CD,我会慢慢地思考,选择几张我先从书里感兴趣的CD,然后再去感受。即便有和他的感受相悖的地方,我也很高兴,并且会一直让这本书陪伴着我,随时默默地和作者去讨论。
吕正惠说他自己是农家子弟,所以常常欣赏同样出身于农家的音乐家的质朴。这恰恰也是我所欣赏的。他同时挺客观,有一篇写歌剧《卡门》和《曼侬》的《痴情的男人往往害了女人》,既站在男性的立场又隔岸体会女性的情感,还不时有点淡淡的幽默感,我真是喜欢极了。
当然他的老婆挺值得同情——他说他的CD已经把快把家人挤得没有落脚地了,走路都随时踢到,还要被他臭骂,而当他心血来潮干脆把某个阶段最得意的CD都摆在客厅的茶几上时,只好请老婆和儿子吃牛排谢罪。这个在旧社会好象叫玩物丧志,可是我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尤其是,在四五十岁,也并不打算再充满野心地奋斗到某一地位的时候,尤其是这样一个充满理解力的人。不过,我还是要庆幸,幸好我是在读这样一个人写的书,而不是这样一个人的老婆!
一本书,还没有从头看到尾就大发感想,充满崇拜,本来是我最不喜欢的。没想到我自己也落到这个窠臼,不过看了头几篇,尤其是看到那篇《谁能了解舒伯特》,我自己几乎要掉眼泪的时候,很难想像我会不再喜欢这个作者其他的文章。
那么让我再做一次感情派吧。
订购这书的时候也有点偶然性,是看到了网上一位购买者的大力推荐,他说这书比同系列的李欧梵什么的写的要好多了。李欧梵那本我看过,觉得写的还可以,所以即便这书只有这么一条孤伶伶的推荐,我还是看在眼里,被牵动了购物神经。
回家时在班车上开始看,先看了第一篇,就是《CD流浪记》,写作者得了意外一笔稿费还是什么的钱,立刻就跑到台北去买CD,从白天买到天黑,逛遍了大小唱片店,在尘埃里把自己早看上的CD搬回家去,回家时风尘仆仆,抗着装满CD的大袋子,既没钱打车又没钱买烟,打电话让老婆骑摩托车接了回去的。我心想,妈妈咪呀,有这么个老公可真够倒霉的。
晚上回到家,因为先试了《费城》的电影原声CD,等着洗衣机洗衣服之余,又看了会努瑞耶夫和玛歌芳婷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把这本不起眼的书扔在了一边儿。直到今天早晨又拿起来。结果一下被吸引住了,简直着了迷。
我看的时候又翻回头看书的作者吕正惠的名字,以前确实没听说过,看他的描述好象是在大学里任教职的,是台湾人。我真该早点认识他呀,就像他那篇《贝多芬,你在想什么?》,他又崇拜又亲近地和贝多芬对话,称他为“你”。
先被震撼了一下的,是他写他的最爱的那篇,《我喜欢海顿》。就像他的标题一样,他表示对一个偶像的无边敬意时,也是很简洁和朴素的,完全不像我这个感情派,老是在某一分钟狂喜得直跳脚,没头没脑的像个花痴。
说到这儿想起来一小截昨天和Cathayan在MSN上的讨论。话题是从他先做了,后来我又要来做的心理测试上起来的。那个测试的主题是看你的性格有多少男性的成分和多少女性的成分,和一切无聊的性格测试一样,把爱读non-fiction、倾向于倾向而不是发表意见……的特征都归入女性范畴,所以Cathayan和我和大多数人,都得了女性气质的毛病。Cathayan当然一笑置之,我却很懊恼,因为老以为我是有些男性气质的。我跟Cathayan说,我是感情派,我期望我自己70%是感情,30%是理智,Cathayan说,应该是反过来才对啊!我说为什么,你们那么理智的,根本体会不到激情、热情和狂喜,Cathayan说,在理智的基础上一样可以有激情、热情和傻笑,而且可以体会得更深刻(我还问他我目前是怎么样的比例,他说是50%对50%)。
随着近半年对各种乱七八糟东西的心得和体会,我不得不承认,他这话是对的。
而看这本《CD流浪记》,我立刻更深地体会到了这点,而且,我感觉到,这位吕正惠的行文、口吻、表达感情的方式和内在的那种宽阔的包容力,不偏不倚,正是我所追求和期盼看到的那种。
我对古典音乐,别说是欣赏者,连入门都谈不到,而且一直是从Wilde、《魂断威尼斯》、Ferrinelli那些电影里汲取断简残章,直到去年才听了第一场完整的现场音乐会。但是好象随着对舞蹈的喜爱,对音乐的渴求也越来越多,虽然没有刻意地买CD(我买的影碟已经够多的了,实在负担不了),但电视遥控器的常用键除了几个电影和播历史频道节目的频道以外,也常常被按到以古典音乐为主的音乐台。
以前听音乐时,最大的感受莫过于,电影、绘画、小说戏剧和舞蹈这几样,都太倚重于欣赏者个人的经历,搀杂了很多后天的东西,比如所受的教育、知识、价值观……等等,而音乐是直指人心的,更偏重于人先天的性格。我听过一首海顿的交响乐,就完全不喜欢,一点说不上原因。
现在看了吕正惠说海顿的这篇,我才明白,首先音乐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当然仍然要听凭自己从自己内心里去欣赏,而不是去听评论家的),其次,我之所以不喜欢海顿,可能就是太片面化太简单化,或者说太感情化地得出自己的结论了。当然,可能把海顿买齐了,买来各种版本,我也可能仍然不喜欢他,但那时,或者有可能得出建筑在理性之上的感情了。
所以,我觉得吕正惠的这本小书,最让我着迷的就是,他自己有一个宽阔的心胸,并在字里行间使得别人也变得心胸开阔,可以敞开胸襟去看这个音乐的世界,把自己变得很少,美妙的世界就变大了。
另外,对于我,这本书真是最好的入门指南,因为他可以容纳的空间很大,所以他谈论的范围普遍到了几乎所有最著名的作曲家,还有我也越来越感兴趣的歌剧。同时,由于他那成千上万的CD,常常是每晚3数小时的聆听,对音乐家作品的熟悉和对音乐家生活背景的熟悉,和广播的同情心、理解力,常常让我这个阅读者散发同样的感慨。我并不急于马上按着他的指引去买CD,我会慢慢地思考,选择几张我先从书里感兴趣的CD,然后再去感受。即便有和他的感受相悖的地方,我也很高兴,并且会一直让这本书陪伴着我,随时默默地和作者去讨论。
吕正惠说他自己是农家子弟,所以常常欣赏同样出身于农家的音乐家的质朴。这恰恰也是我所欣赏的。他同时挺客观,有一篇写歌剧《卡门》和《曼侬》的《痴情的男人往往害了女人》,既站在男性的立场又隔岸体会女性的情感,还不时有点淡淡的幽默感,我真是喜欢极了。
当然他的老婆挺值得同情——他说他的CD已经把快把家人挤得没有落脚地了,走路都随时踢到,还要被他臭骂,而当他心血来潮干脆把某个阶段最得意的CD都摆在客厅的茶几上时,只好请老婆和儿子吃牛排谢罪。这个在旧社会好象叫玩物丧志,可是我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尤其是,在四五十岁,也并不打算再充满野心地奋斗到某一地位的时候,尤其是这样一个充满理解力的人。不过,我还是要庆幸,幸好我是在读这样一个人写的书,而不是这样一个人的老婆!
一本书,还没有从头看到尾就大发感想,充满崇拜,本来是我最不喜欢的。没想到我自己也落到这个窠臼,不过看了头几篇,尤其是看到那篇《谁能了解舒伯特》,我自己几乎要掉眼泪的时候,很难想像我会不再喜欢这个作者其他的文章。
那么让我再做一次感情派吧。
11:05:00 -
barb -
10 March
卡拉华治奥
看港台中文作者的书就是这点不好,一个外国人名依着方言译成颠三倒四的名字,印成白纸黑字更不知道他说的是啥。迈克的一篇文章说专程从法国坐火车到米兰,丢下行李就跑去博物馆,求卖门票小姐“只看卡拉华治奥,只看卡拉华治奥”。我脑子里不成器的搜索引擎急急开动,到底没想出这是谁来。另一篇文章又说,在维也纳的美术馆见到三张卡拉华治奥,馆里那么多张椅子,惟独它们面前一张被坐到坐垫起毛。
这种popular的大师,我这种流行附庸没理由不知道哇,搜肠刮肚的好急。后来,忽然从一句话里寻到蛛丝马迹,说是,“停在那篮我垂涎已久的水果前”,这下就呼之欲出了,还有谁。我所熟悉的那个名字是卡拉瓦乔,Caravage,丹纳的书里,被傅雷译成“卡拉华日”(傅雷翻译人名不知遵循什么方法论,一个个顶不可爱,提香,竟然译成“铁相”,比亦舒的“鲍蒂昔里”更离谱)。
印在纸上的卡拉瓦乔没精打采,颜色暗靡靡,就除了一盘又一盘诱人的水果,葡萄、桃子、李子、石榴……在幽暗的角落闪着烂熟的光。梨有压痕,苹果上有虫洞,娇艳之余,好象有发酵的酒味扑鼻,溃烂前一秒的辉煌。借着偶像的千里眼看出去,叶上滴着露水,扯近了和卡拉瓦乔的距离。他笔下的男孩儿们却仍然爱搭不理,神色木然,什么琴不琴酒不酒的,色色空空。
又忽然想起来,某期《万象》的封面就是卡拉瓦乔,一阵翻箱倒柜,果然,二零零零年四月,《音乐会》。仍然是他,诗琴演奏者,这次坐在另三个赤膊的男孩中间,仍然抱着那把诗琴,水果悄悄地剩下一串葡萄,藏在左下角。白滚滚像没有性别的身体,痴愚的肉身少年,差点为一期同性恋专题做了代言。这是我猜的,因为有恺蒂那篇《“快把电话拿起来,我不是你妈!”》,又有谈瀛洲再谈王尔德,我又怀疑是编辑找不到那么多点题的稿子才终于做罢,后来发现不是,原来有一篇文章写卡拉瓦乔。
那篇文章叫《黄金》,一个字一个字迸出来,实在看不明白作者想说什么,古龙一样故弄玄虚,只记住了第一句,说卡拉瓦乔的布局饱满得像黄金。《音乐会》状似堕落,少年们朱唇微启,薄薄蒸着一股风情,可是画家没有是非评判,只用重色小心记录青春走向和水果一样的必然的凋零。卡拉瓦乔脾气暴戾,却用这样的精巧收敛的笔浓缩了爱恨情愁,这真奇妙。

这种popular的大师,我这种流行附庸没理由不知道哇,搜肠刮肚的好急。后来,忽然从一句话里寻到蛛丝马迹,说是,“停在那篮我垂涎已久的水果前”,这下就呼之欲出了,还有谁。我所熟悉的那个名字是卡拉瓦乔,Caravage,丹纳的书里,被傅雷译成“卡拉华日”(傅雷翻译人名不知遵循什么方法论,一个个顶不可爱,提香,竟然译成“铁相”,比亦舒的“鲍蒂昔里”更离谱)。
印在纸上的卡拉瓦乔没精打采,颜色暗靡靡,就除了一盘又一盘诱人的水果,葡萄、桃子、李子、石榴……在幽暗的角落闪着烂熟的光。梨有压痕,苹果上有虫洞,娇艳之余,好象有发酵的酒味扑鼻,溃烂前一秒的辉煌。借着偶像的千里眼看出去,叶上滴着露水,扯近了和卡拉瓦乔的距离。他笔下的男孩儿们却仍然爱搭不理,神色木然,什么琴不琴酒不酒的,色色空空。
又忽然想起来,某期《万象》的封面就是卡拉瓦乔,一阵翻箱倒柜,果然,二零零零年四月,《音乐会》。仍然是他,诗琴演奏者,这次坐在另三个赤膊的男孩中间,仍然抱着那把诗琴,水果悄悄地剩下一串葡萄,藏在左下角。白滚滚像没有性别的身体,痴愚的肉身少年,差点为一期同性恋专题做了代言。这是我猜的,因为有恺蒂那篇《“快把电话拿起来,我不是你妈!”》,又有谈瀛洲再谈王尔德,我又怀疑是编辑找不到那么多点题的稿子才终于做罢,后来发现不是,原来有一篇文章写卡拉瓦乔。
那篇文章叫《黄金》,一个字一个字迸出来,实在看不明白作者想说什么,古龙一样故弄玄虚,只记住了第一句,说卡拉瓦乔的布局饱满得像黄金。《音乐会》状似堕落,少年们朱唇微启,薄薄蒸着一股风情,可是画家没有是非评判,只用重色小心记录青春走向和水果一样的必然的凋零。卡拉瓦乔脾气暴戾,却用这样的精巧收敛的笔浓缩了爱恨情愁,这真奇妙。

08:56:00 -
bar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