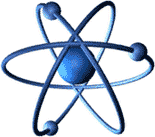Jump to navigation
Barb的不老歌
30 January
一坛醉生梦死的酒
然而还是看了王家卫。导演王家卫、摄影杜可风、美指张叔平,这三个名字像宿命般击中了我,一个又一个喃喃低语的片段,像幻灯投于白墙般于我心里留下痕迹。
95年入学后,遇见了一个可以一辈子一起说电影的人(不是家猪)。她现在在拉萨,那时在我的班里进修。就像是昨天的事,在外教Lina的家里,她坐在藤椅上,我蹲在她身边,一场又一场电影说下来,两人恨不得携手同归电影的大梦(归彼大荒)。那时我俩说得最痛快的就是《重庆森林》,因为身边没人爱看(不像《花样年华》后,王家卫一时风行,鼎鼎大名,如星巴克般灌耳)。
说到最细处,不外乎警察663坐在马桶上对香皂说:“你知不知道你瘦了?以前你胖嘟嘟的,你看你现在,都扁了,何苦呢?要对自己有信心。”对毛巾说:“我叫你不要哭嘛,你要哭到什么时候?做人要坚强一点嘛,你看看你,窝在这里象什么样子?”对毛公仔说:“怎么不说话?别生她的气了。每个人都有不清醒的时候,给她个机会,好不好?”
还有《阿飞正传》里,旭仔那“十六号,四月十六号。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号下午三点之前的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这是事实,你改变不了,因为已经过去了。明天我会再来。”
《堕落天使》中,哑巴阿武想:“每天,你都会和许多人擦肩而过,他们可能会成为你的朋友或是知己。所以我从来没有放弃和任何人擦肩而过的机会。有时候搞得自己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行了。那天晚上,我又看到了那个女人,我知道我可能不会和她成为知己或朋友。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擦肩而过,衣服都擦破了,也没有看到火花。”李嘉欣坐在摩托上,紧紧伏在他身后,“走的时候,我叫他送我回家。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摩托车了,也很久未试过这么接近一个人了,虽然我知道这条路不是很远。我知道不久我就会下车。可是,这一分钟,我觉得好暖。”
穿过了时间和空间,我相信当年很多人会从他的电影里看到自己。许多许多的感情,只是一分种擦出的火花,过后将湮灭于何处,谁会管它?
后来结识的很多爱电影的朋友,会评选自己心爱的王家卫电影,多半是自己被那片刻光影击中的一刻。《重庆森林》可能不是最好的一部,可由于95年被它击中后,受了重伤,所以它成了我最喜欢的王氏电影。其实跌进电影里面,是有点痛苦的,在活在别人故事里的不到2个小时中,生关死劫,一一感同身受。
在王家卫拍得最美的一部,《东邪西毒》里,异样苍凉的天色下,数段纷乱的感情,几个落寞的人,你,是哪一个?又或者,你是等待一句“不如重新开始”的黎耀辉,他说:“一直以为我跟何宝荣不一样,原来寂寞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一样。”
Liar曾经用“流烟非雨”这个ID写了一篇关于《东邪西毒》的文章,里面一段话他可能觉得煽情,但我喜欢:“无非是一杯清酒就可以湿透了你我的前世今生,无非是一句轻轻的爱语就可以击穿了你我的灵魂,无非是那么一段浮云掠过的情感就可以耗尽了你我的一生,无非是那么一个不再出现的身影就可以烙印在你我本来浅薄的生命。”
如他所说,这些全都是王家卫的锋芒,而王家卫身后的杜可风、张叔平,谭家明(剪辑)的光芒似至柔而隐忍,流淌在电影的每个片段中,所以不被人发觉了。《东邪西毒》里美丽的景色,我觉得无双,是《卧虎藏龙》、《英雄》都比不了的。猎猎大旗,漫漫黄沙,纠缠其中的那几个人,是张叔平的功劳了,以至以数年后周星驰在《大话西游》中仍在向盲武士致敬。还有西毒的大嫂,张曼玉那美丽的群裾,手中拈的一朵花,颊边的胭脂色,她轻轻地跟东邪说:“以前我认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有些话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一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分别,有些事会变的。我一直以为我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看着镜子,才知道我输了。在我最美好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人都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
写到这里,写不下去了,耳边只听到那几个声音……
“不久前,我遇上一个人,送给我一坛酒,她说那叫‘醉生梦死’,喝了之后,可以叫你忘掉以做过的任何事。我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酒。她说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如果什么都可以忘掉,以后的每一天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你说这有多开心。 ”
“没有事的时候,我会望向白驼山,我清楚记得曾经有一个女人在那边等着我。其实‘醉生梦死’只不过是她跟我开的一个玩笑,你越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忘记的时候,你反而记得清楚。我曾经听人说过,当你不能够再拥有,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
也许电影就是这样一坛醉生梦死的酒,你越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忘记的时候,反而记得更清楚。
28 January
浮云
《浮云》是成濑巳喜男的一部电影,曾计划去北京的雕刻时光Café看的,始终未能成行,这个名字却印在心里。想象中它是如小津安二郎的电影般波澜不惊,按关锦鹏的形容,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在有如浮云般的往事中,95年是我看电影的里程碑,正是在这一年,我清楚地发现电影于我不只是一场娱乐。香港无线电视的一位女制作人曾说过,金庸的书教她作人(忠、孝、节、义)。我的成长,我的世界观和审美观,隐约中也被电影左右着。
在95年之前,我已从电影之小中见识了世界之大,而这芥子与须弥,不亚于书。
95年以前我看到的好片子还是在电视上,很多从小说改编而来,却有一个比书更辽阔的空间,像《霍华德庄园》,像《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看了这两部电影,我不得不喜欢安东尼?霍普金斯和艾玛?汤普曼。或者,奥斯丁和哈代笔下,英国的绅士与淑女从来不是俊男与美女。只是这样平凡的样貌和无尽的隐忍,只是一个眼神,甚至只是连眼神都不敢交会的含蓄,已经让人茫茫岁月中自己只似一粒微尘。
这几个片子不是中央台看的,而是家里地方有线台,不知哪位领导突发神经,只放了一小段时间,都便宜了放假在家的我了)另两部好片子《大河恋》(A River Runs Through,罗伯特?雷德福导演)和《好人寥寥》(又翻译成《义海雄风》)也是这时看的。〈大河恋〉里第一次惊见布拉德?皮特,这个酷似雷德福(亦舒也提到过数次劳拔烈福,就是雷德福)的男孩把青春表现得再无余地,片尾华年而逝,那真是一把青春烧成了灰,导演也了无遗憾了。《好人寥寥》上个月中央台电影频道又播过,重看不免感叹汤姆克鲁斯、戴米摩尔和凯文培根当时的年轻(落花流水春去也),就连杰克?尼克尔森也不过是个中年人。过往的一出出电影,像记录片,记录着荣与衰,和这么多人曾经这么好的青春。
这中间还看了一部吓人不轻的恐怖片,《比留子》。看的时候是个下午,我一个人缩在墙角,手心流着汗,死死捏着一个枕头。这样恐怖的故事(我觉得恐怖过《午夜凶铃》)竟然有那么美的画面,且结构极严谨,让人边怕又忍不住看下去,从此对日本人的心理恐怖领教了)8O
到95年的时候,我考到了后期本科,可以到北京上学,行前,去南宁参加了一场笔会。记得真真切切,那个炎热的夏天,邕江汩汩流水声中,我看到电影院牌子上4个大字:《重庆森林》。身边有人讨论:“咦?这个名字怎么这么怪?”“我看过,一点儿也不好看,看不懂。”这一次,我和王家卫的电影失之交臂。
流年
在1995年之前,看电影完全是无意识的,而且多半是看中央台。
那时常和妈妈一起看秀兰?邓波儿系列,从《小叛逆》到《亮眼睛》。后来从报上读到这个可爱的女孩当时正受着公众无处不在的骚扰和巨大的心理压力,有点瞠目结舌。现在想想,秀兰?邓波儿该是多么一个早熟的女孩,她的十几岁似人家的一世,是把生命浓缩了来用的。
那时候的中央台每周末的国际影院真是大恩大德,老播一些在国内名气不大却真正经典的片子。我最喜欢的一个叫《一个漫长炎热的夏日》,最喜欢那个灰眼睛的男主角,眼神深到不知名远处,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叫保罗?纽曼,这部片子是他与妻子同演,得过当年的金棕榈。
另一出也是极喜欢,叫《朱门巧妇》,保罗?纽曼是豪门叛逆子,他与老爹的争执和感情戏火花四溅,伊丽莎白?泰勒是夹在其中委曲求全的女人,这出戏让我唯一一次对她有了好感。
其他的,还有《青山翠谷》(有格利高里?派克)、《费城故事》(凯瑟琳?赫本和加里?格兰特主演)、《彗星美人》(是部给天下女人看的好片)等等。那时印象最深的是每次片头21世纪福克斯的大字,以及米高梅的醒狮标志。
如果恰好有观众钟爱的片子,央视会拿来一遍一遍重映,这个名单必然包括《罗马假日》、《希茜公主》和《魂断蓝桥》。还是从言情小说上知道,那时奥黛丽?赫本的“妹妹头”在台湾曾经多么的流行。她的清丽,罗密施奈德的微笑,和费雯丽惊世的美貌,不知曾是多少男士的旧梦(“微微风,涌起旧梦,拾起一片回忆如叶落……”)。
然而怕见伤悲,我忍到很多年后才第一次看全了《魂断蓝桥》,当时却不小心看了另一出悲剧,《梦断花都》(他是记者,她是物质女子,他成名后,她堕入浮华无法自拔,渐渐理想分歧,一个夜里她醉酒夜归,他不去应门,竟致她在雪中受冻而死。当爱已成往事,他竟是没有责任的吗?)。
除了剧情片,最最感激中央台还常放另两类电影:歌舞片和希区柯克的悬疑电影。《雨中曲》不用说了,如一切旧日时光,永远是那么美。有一出印象深刻的,好象叫《红菱艳》,亦舒在小说里提过,是一个爱跳舞的少女穿上了梦想的红舞鞋,却不能停止地(恐怖地)永远地跳下去。要到这时忆起,才觉得当年好莱坞的编剧是多么好(能不忆江南!),除了梦一般的画面,竟还要灌输人思想)
希区柯克电影,是亦舒笔下女主角在夜半无事时爱看的片子,似乎也成了品味之一种,但实际上老先生的心愿是吓天下人,而不仅是白领女子:)看看《牙买加旅店》吧,那才是心理恐怖的老祖宗。《蝴蝶梦》和《煤气灯下》好象又偏浪漫了,《后窗》、《谜中谜》、《西北偏北》则带着惊悚,到了《鸟》却像走火入魔了)
前几天蒙朋友送了一本杜可风的《放色海外——非中国电影笔记》,里面记录的正是他在好莱坞重拍希氏《惊魂记》(Psycho),的经历。然而即便是他,亦无法复现大师的原貌,毕竟,陈年的煤气灯,暗夜的氤氲,旧日优雅的气息,是高科技下镁光灯再难复制的美色。
然就是杜可风,在这本书中说了我最喜欢的关于电影的一句话:电影既是亲近,又是距离,A space of a kiss。及至多年以后,我才回味过来这无限近又无限远的瞬间。那时,已在电影的梦境中一头栽了进去。
21 January
《纽约琐记》和林风眠
终于买了陈丹青的《纽约琐记》,越看越兴奋。记得以前帮朋友买这本书时它还一度缺货,就是因为替朋友买多了,自己也想买(书是上下册塑料纸密封,所以买了也不能翻看)。第一个托我买书的是在拉萨的最好的朋友,她的丈夫边巴是位画家,当时将要去纽约办画展、作画,听说有这本书就等不及在拉萨找,急匆匆地托我买了寄去。陈丹青的一部分名气恰好也是因为毕业时画西藏大画。有一次看中央1台“美术星空”(这个节目挺好看,可惜总是白天放),陈丹青的师友回忆这段事,陈丹青从西藏回来、从箱子里取出画的样子仿佛历历在目。第二个托我买书的,是好友的表姐,曾在藏学研究中心翻译藏学资料(藏文译成英文),表姐比我的朋友长得更像藏族,但又很古典、美丽,长发天然卷曲,她因为不喜欢而盘成髻,偶尔披散下来,是要让人惊艳的。她在旧金山呆过一段时间,可能是异域的经历,又是一个喜欢古典气的艺术的人(她喜欢的片子,都是《钢琴课》那种类型)(陈丹青自己,活脱是古典长相),她一听我给表妹买了这书就立刻托我代买。
看陈丹青激动起来,是因为《纽约琐记》不是一本纯谈艺的书。看时突然觉得,很多对人、事的看法,真不能让搞文字的人来说——要让另有专业的人闲闲看来,总有惊人之处。前几天看张五常《凭栏集》,印证这个想法。他的《经济解释》最流行,我没看过,也不感兴趣,买《凭栏集》是为了里面提到书法和印章,可以送给写书法的叔叔,送前自己先看一遍(幸亏没有塑料密封),对前2/3的文章不感兴趣,甚至反感其张狂(不断引用别人表扬他的话夸奖自己,惟恐别人不知),但看到他写林风眠的一篇,立刻倾倒。
林风眠(一直欣赏大师这个名字)是广东梅县客家人,一九OO年生,少时被乡里认为是绘画天才。后来的名气,一直是国画大师,张五常却对此作惊人之语,称他为“印象派最后一位大师”。林风眠一九一九年跑到上海碰运气,考取奖学金留学巴黎。彼时印象派大师在巴黎势起,“当毕加索在巴黎大叹倒霉之际,一个梅县小子正在巴黎的艺术少林寺内尽得真传。当时外人不知道,而林风眠自己也似乎是不知道。”他回国后,经文革一劫(林亲手毁画二千,入狱四年),于七七年去港,定居太古城,好象突然心生自由,“专注于画事,一时间少年时从巴黎学得的印象派绝技表现无疑”,此前,他留下的作品都是传统国画。印象派始于十九世纪中,谁是创始者难有定论,但张五常断言,印象派终于一九九一、香港太古城,它最后的代表人是林风眠。这篇文章文字很漂亮,数语道尽大师曲折一生(他说林风眠的遭遇“是时也、命也、运也”,放在文中,极尽苍凉),我很佩服,张五常这时把自赏之语不遗余地奉送给林风眠(尽管有朋友说,那是因为林风眠不是经济学家:)。
陈丹青也是写人,写他在纽约遇到的,怀才不遇的艺术家朋友奥尔。奥尔是罗马尼亚人,恰好我妹妹大学学罗马尼亚语,虽然对这个国家一直没有好感,但对这么一个小国的艺术成就还是有点佩服的(罗马尼亚画家巴巴前年曾来中国办画展)。奥尔是那种纽约随处可见的没受过正规美术训练的画家,由于对艺术的狂热不断作画,罔顾生活,而且喜欢的是西洋古画(卢本斯)。陈丹青说他希腊式的面容俨然就是画中人,“瞧着他和他的画在一起,就像面包抹着奶酪、刀叉戳在烤牛排上那股劲!”。这个十八岁的少年,经过十数年痴心不改,用未经科班训练的不成熟技巧、一心画在纽约再没什么市场的古画。期间娶妻、生子,不停打工(竭尽全力抚养妻小),不停作画,面对画商会脸红,对着堆在画室中无法卖出的画会愤怒(被木杠戳得满脸是血)。
三十几岁的奥尔终于得以在一个阔人家做了一副墙面画,所有不成熟的技巧及激情混杂出“奇怪、动人的效果”(真想看看这副画),当然,画中希腊神话、圣经故事、罗马战役中种种角色仍然简约为他一直的模特:一家三口(书中附有奥尔及妻子斯苔芬妮的照片,二人相貌均古典、俊美)。陈丹青说是:
我仍然没说心里话。是的,我理解他,因而怜悯他的挣扎,我比他还要感谢那位房东给他机会,付钱让他疯狂;但凭什么我怜悯人家?这位‘罗马人’勇敢而无望地扮演着欧洲古典艺术的当代英雄,我尊敬他。就人种和文化而言,这理应是他的梦想。多年来我难以调和对奥尔暗藏的怜悯,现在我可以释然于心;这壁画给了我尊敬他、赞美他的机会。
来广州前,箱子里本来只放了两本书,林怀民的《云门与我》和朱天文的《花忆前身》,这下,想再放一本《艺术手册》(The Art Book),没事时看看画,虽然不懂,但艺术或说是让人感动/献身的东西,都是触类旁通的。
游园惊梦
这个名字,拿来写小说最好,字字透出昆曲的丝竹声,但我却想拿它来写一个人,一个多数人心中俗不可耐的明星。
说他俗也真是,出道时土得可以,而眼前一双大眼也失了势——现如今流行古灵精怪的男人,如陈弈迅般搞怪才出位(不过这一位我也是喜欢),大眼如F4般的男人很难赢得人的尊重(看也还是爱看的)。
更让人难堪的是他唱歌曾经那么难听,难听得他后来再有什么好歌也埋没了。最近再听到他三数首好听的“老”歌,已如前尘往事,一首是《望乡》:
长街上满是熟悉人
笑容仍热似艳丽阳
回忆外却是漫天凉
处人群内也是仍孤独
离乡後我是异乡人
每回头望觉路长
盼我家乡朋友都快乐
而父母也健康、心舒畅
你於思海仍那麽漂亮
离别你,每天都觉漫长
涂改是岁月专长
有谁能没变样……
另一首是《信鸽》,似脱胎自席慕蓉的诗,不那么文艺了,回忆却更绵长:
我打开窗户
细细地阅读
你亲笔用心所写下的情书
爱是漫漫长路
孤独、乐与苦都不堪细数
如果这一生
只能用思念
系住每一刻的魂萦和梦牵
就像信鸽一样地飞翔
千山万水不停飞
我敞开我心扉
而我只愿对你倾诉生命的全部
像开了花的树
站在你经过的路……
还有他的《春眠》,以粤语(据说粤语是古音犹存)念出: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古诗表不尽 心内的狂潮 夜阑人静处 孤独可明了
想你从不变 春梦的微笑 生来的爱慕 怎也忘不了
缠绵的邂逅 失落的苦笑 恋恋仍思念 只恨路遥遥
正似一个倾慕若狂的男孩正在为情所苦,此恨缠绵,叫我想起亦舒的《连环》。
然而喜欢他还不是因为这些,而是见他跳舞——是某次颁奖礼上,他带了舞群跳《爱定你》,西班牙舞,他跳得青春迸现,气势直逼Flamingo的《卡门》。顺带说一句,看他跳舞一定要看现场录制版,因有次看他跳《一变倾城》,那段充满嘲弄的“I love you, you love me, everybody……”时,作木偶状,简直连眼神都神似。想起他28初尝红滋味,如提线木偶般被操纵,全无灵魂,终于受红颜知己所谏渐渐摸出一条生路时不免感慨。当时曾有圈中人(文隽之类)撰文批判艺人跳舞时假唱现象,说只有他是不欺场的,一场演唱会17首歌中有13首要跳舞,每一句都是现场唱的。可能认定这是他唯一本钱,不吝惜一点力气。
若想看他最盛时舞姿,我有一个MV推荐,《神经》。看时我纳闷,这人,怎么每块骨头都会动?(“神经,早已经,扭转滴答心跳声……神经,都已经,涌进疯癫的爱情……”)可惜这种才华早被忽略,只有音乐、电影可以批量炮制,跳舞是太小众了,以他的水准,其实可以去跳云门。
电影,是忽略他的又一个所在,嘉禾竟然签他作动作明星(“舞”艺终于获得承认)。我其实最爱看他在《安娜玛德莲娜》中,那个诡诡一笑的游牧人,那一脸纯真的浪荡公子。人皆说黄耀明是堕入凡尘的小王子,我只道也是说他。
某年一次颁奖,他终于得到最重要的一个奖,观众票选最受欢迎男歌手奖(这个奖的得奖专业户一向是刘德华),席上他放肆地和小美抱头痛苦。他的这位红颜知己实为诤友、不亚于林夕的词作者,童花头,素净、骄傲。据说她劝他转型后,本想移民加拿大,但因四处流传他和她的绯闻,她一气之下留港,为他写词,作他的经纪人。她那些美丽的句子亦因他“唱得不好”而埋没了许多。
后来,她为他写词的《游园惊梦》得奖,他似是平静地说:“这是我第一次不靠快歌得奖。”这时我惊觉,我已在听郭富城的CD了。
今年他已年近四十了吧,新人涌现,他与同辈快被称前辈了,这一口青春饭不知要吃到何时,套句亦舒的话,不是不悲哀的。
20 January
电光幻影
蔡澜的《电光幻影》,合了金庸爱用的一句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可能蔡澜就是如此看电影,复以书名嘱影迷:当作如是观。
没看到过如此跳脱的影评人,可能太久浸润行中,吃过这一行的苦,也尝过这一行的甜,作为制片人,这苦和甜可能与导演、演员的甜苦统统同归而殊途。写到电影人一节,看他懒散道来,也就是闲话家常,文字不动感情,当时情景之惊险、之感动、之幽默却又历历再现。像写成龙在南斯拉夫拍戏受伤一篇,那么高的台子,他一跳,工作人员都说动作太完美,成龙自己认为不行——一举一动不够清楚,“流”了;再一跳,够清楚,成龙认为不行——看准了目标跳,不象被人追杀,于是又跳——这一跳摔到地上,耳朵流出血来,这几下子且只是全篇铺垫,吓吓人,后来写到南斯拉夫猥琐老医生,又叫人笑——大家哪敢让那衰老头治成龙,但是情势危急来不及去别家医院,又叫陈自强打听到南斯拉夫最好的医生是彼得逊,众人大叫“我们要彼得逊医生来开刀!!”——“其貌不扬的猥琐老头微笑地对我们道:‘别紧张,我就是彼得逊医生。’”把我笑坏了,手术半途老医生且跑出来抽支烟再进去——真是个活剧。蔡澜才把笔拉回成龙身上,彼得逊说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一个病人,从他进院、照X光到动手术,血压保持一定,没有降过,真是超人,真是超人!”——蔡澜写电影人,我最喜欢这篇,两个主角互相牵带着,活了。成龙做事认真、敬业、体质超强、控制力一流,老彼医生邋遢、幽默、镇定、医术高超。该篇的结尾是:
“我们三星期后继续拍摄,不影响戏的质量,上次失败的镜头,还要来过。
成龙说。”
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描写,是说蔡澜给大岛渚当翻译一段,金马奖彩排,大岛渚在后台看着倾斜度高的塑料楼梯心里发毛,扭头对蔡澜说:“是不是大丈夫?是不是大丈夫?”(日文“大丈夫”意为“不要紧吧?”)蔡说:“当然大丈夫,我们拍外景什么山都爬过,这点小意思,大丈夫。”——“大岛觉得有理,又大点其头,嗨嗨有声。”颁奖正闷,倪匡偷偷喝酒,“道貌岸然的大岛一手将瓶子抢过去,大口吞下,速度惊人。”倪匡大笑,说:“喝酒的人,必是好人!”“大岛即又点头嗨嗨。”——大岛渚在我心目中一向是那拍《感官世界》、《战场上的快乐圣诞》的放浪不羁惊世骇俗的导演,简直于心目中都觉得他才华之余有些变态,给蔡澜一写,却像个糊涂大醉侠,“嗨嗨”之声,只见老实,不见放浪——多得蔡澜行文简洁,虽略见粗糙(港报专栏人通病),但往往重现趣景,让我在等车、排队的时候也看得下去,有这样成就的影评人,我见得不多。
从蔡澜回想我看过的一些影评集,文天祥的《影迷藏宝图》也好,陈辉扬的《梦影集》也罢,无不象论文,需要耐性,用力咀嚼。迈克写《影印本》,可读性强得多,然而太绮丽,浓得化不开,仍是要一看再看三看才好(我心里常把迈克比作柳永)。一开卷便让人笑,随时也可开始,随时也可结束的,只有蔡澜一个。虽然有时过分粗糙,但读影评,趣味耳,时时求完美只怕没的读。虽然迈克永无例外地列席我心中最爱的影评人榜首,但叫我像看晚报似随看随丢,做不到。我最贪吃,拿吃来比,迈克象生牦牛肉干,鲜艳浓缩不加调料而味道激越,吃不到也想,蔡澜就是菜根,纵有香味,仍份属家常,吃的时候高兴痛快,吃不到的时候也就忘了,想倪匡黄沾蔡澜几人友谊,不知是不是这家常味。
以上是蔡澜写电影人,虽然简略,而无不怀着悲天悯人心肠,他写电影也是这样。
有一部丑女孩莫莉?灵活(MOLLY RINGWALD,“心灵捕手”里演马特达蒙的女友,我当时惊异她的红和丑)的片子“永远”,按蔡的说法是老套又俗不可耐的故事,但“我们做观众的,要是觉得粤语残片太旧,那我们可能已经长大;但是,我们同时不能接受年轻人的片子的话,那么,我们并没有长大,我们只是丧失了赤子之心。这是多么可悲的一回事。”
给我印象深的是,蔡澜从不一意刻薄,比如写到恶心而古怪的《畸形》,也是直白地讲完故事,再加几句个人观感,而从不煽动任何读者从自己角度想问题,再比如写到法国人尚?克库图,他的诗与画是“在美之中有噩梦,噩梦之中有美”,并无主观的评判,只描述他对后世的影响力,对于读者而言,这太善解人意了——在读过的那么书里,我们从来都没缺乏过富有煽动性的热情。
他的影评我最钟爱的有两篇,一是“望乡”,通篇不象一篇影评,倒象一篇熊井启的传略,一个导演的人格和理想尽在其中,“望乡”的几个女演员倒成了配角,栗原小卷是深明大义,一力担当最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报酬还是其次;高桥洋子的戏演得自然而激烈,有裸着身子奔入院子痛苦一场,蔡澜说“戏是那么自然和必须,删剪这场戏的国家,是落后的国家。(这戏我还没看过,想象中当年必然剪了)”;田中绢代,无论在文章中还是在影史,都是当仁不让的演艺女皇,蔡澜的评语是:“无懈可击”,——电影从来都是一群人的心血。从熊井启在新加坡对日本妓女墓的凭吊,到一部反战电影的出炉,我们看到日本导演及演员的良心,蔡澜似个魅影,把阑珊往事一一在我们面前演映,我们却知道匆匆电光,并非幻影。
另一篇其实不是评电影,而是评摄影技巧,题为“该死的镜头”,英文ZOOM,蔡译“冲镜头”,能够在同一画面由远景一下“冲”成特写,或做出相反的效果。蔡澜举了个例子,说某种剧情下不是“冲”镜头能解决的,非铺车轨慢慢摇近镜头——因为“镜头的持重,才能把剧中人的感情携带出来”,看到这里我几乎有些感动,世道一直淡,蔡澜作制片应该只是管钱的,却为电影投注这么多感情,细节仍用心剖析——看他评《黄土地》,处处为影片的破绽辩解,仿佛当电影孩子一般,一个职业电影人(还是斤斤计较金钱的)能爱电影(并同时默默关注电影人,哪怕再小的配角)到这个地步诚属难得。
当然还有好多搞笑之作,象“香港喷烟机”——外国人用机器和高科技造电影烟雾,香港人用四方石油铁桶,顶一掀,烧几把拜神的香丢进去,熏一会再打开,浓烟立喷——方便快捷,又比化学药品烟雾便于扑散,叫美国同行叹为观止。搞笑时也孩子样——在我印象中的许多媒体报道上老把黄沾倪匡蔡澜几个当作搞笑老友,好象随时都能唱起黄沾与徐克合唱的那首“沧海一声笑”(在那个版里,他们还是真笑,几个破锣似的嗓子,又搞笑,又豪迈)……
某年,看烂糟糟的“Gay佬四十”,只记住了“KK”——吴镇宇的眼睛,和一个在陈小春身后背景里走过的花白头发,因为当时老觉得眼熟,却死活想不起来是谁,现在一想,扮路人都那么一本正经的,还有谁——不就是蔡澜。
玩蜻蜓
蔡澜
我们那时大家还年轻,坐在广阔的平原上等太阳。已经是秋天,芦苇长着白花,风一吹来,我们像是沉浮在白色的大海。
前一天晚上打电话打到三更,国际台还是接不通,只好放弃,但王羽把这件事挂在心上,一整天闷闷不乐。
“我不拍了。”他忽然间说,也不怕把那套全白色的戏服弄脏,一躺就躺在芦苇丛里,不见了人。
他是男主角,天皇巨星,说不拍就不拍,谁能拗他?消息传到导演张彻那里,他跺跺脚,望着天,猛抽他的雪茄。
一群人四十多人,老远地跑到日本出外景,吃住就是一大笔费用。我负责制作,处处要预防浪费,更是心急如焚。
“等收工了我再替你接电话。”我说。
“那么迟了还没有人听,你说她到哪里去了?”王羽越说越气愤。
“或者去看午夜场了吧。”
“是啊,也许是去看午夜场了。”王羽说完坐了起来。我们又有了生机。
“但是,不对呀,”他想了想,“昨晚是星期二,哪里有午夜场?”
我也说不出话来。
“会不会到朋友家去打麻将。”他为自己解答。
“对,对,打麻将。”我这么一应,他反觉不妥。
“我马上回香港。”他决定。
这事已弄得不可收拾了,有什么办法挽回?
天上飞来一群红蜻蜓,有一只停在我面前的白花上。我静悄悄地伸出手指在它的眼睛前面画圈圈。蜻蜓有复眼,圆圈越画越小,它变会头昏,等它心迷,更能一把抓住。
王羽看得神奇,也找了只蜻蜓画圆圈。一抓,让它飞走,再找来画。
大家看着这两个疯子画圆圈。郑佩佩、午马、杨志卿,甚至张彻也拿着雪茄画圆圈,把所有的事都忘却了。
太阳出来,我们继续拍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