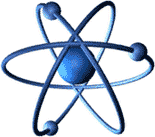Barb的不老歌
24 January
西斯廷
二进梵蒂冈,直冲博物馆。馆藏没有想象中多,但因为空间大,有宽大走马铜梯,有庭院,有长廊,很适合遛来遛去。讨厌的是绘画室很难找,我绕出绕进外院的大洋洲土人展和冷僻的石碑展,好不容易才摸到绘画室的入口。
他们的绘画数量和质量远不如波盖赛,赫赫有名的埃及馆也不如雅典考古博物馆(更不要提横征暴敛的卢浮宫)。古雕塑如拉奥孔、壁画如拉斐尔画室固然珍贵,毕竟数量有限。如果有什么让梵蒂冈不可取替的,只能是游客争抢立锥之地的西斯廷(Sistine Chapel)。我大步流星挤进这团混乱,登时目瞪口呆。
一面墙的末日审判(The Last Judgment),一团团一摞摞活动的肉体,非常挤逼地zoom in。我把天顶上的上帝创造亚当都给忘光了——那个手势何其温柔,哪有这么风卷狂云式的无穷动。Jun曾说站在西斯廷天顶下,立刻觉得米开朗琪罗是喜欢男人的。看多了印刷版的米式(雄赳赳的)肉体,我也以为自己会是这个感想,没想到站在人海里,那么夺魂摄魄的一刻,竟然感到一种超脱肉体的英雄主义,何其壮烈的人的创造。难以想象和我们一样的肉身凡胎,再寻常不过的颜料画笔,一笔一笔再工整不过的技艺,能泼洒出这么腾空而起、铺天盖地的精神力量,神迹竟出脱于人手。
到这一分钟才明白米开朗琪罗对同时代艺术家如达芬奇、拉斐尔的不屑从何而来。他们如果是顶尖儿大师,米氏可称造物者的信使,使人造如自然,彰显鬼斧神工。
教皇庇护四世令米氏的朋友搞过一个“穿裤子”工程,给末日审判里的裸体画衣服,有树叶、有兽皮。当时的非议者焉知画的是肉体,主旨却在肉体之上呢,譬如众志成城是靠人的力量,没有肉体,哪来精神。他们看到的不过是自己的心罢了。
而米开朗琪罗对绘画竟是不屑的,他最讨厌别人称他画家,他宁愿别人叫他石匠。他毕生的光阴、健康全消耗蹉磨在采石、运石、雕刻、半途而废再重新来过上。末日审判动人的地方,好象是真人变化成雕像,雕像又变化成绘画,憋着全部力量凝结于壁,只需一声号角,就能活生生崩天裂地。是平面的雕塑。
旅途里看傅雷译《巨人三传》,罗曼罗兰不胜惊讶地列举米开朗琪罗的弱点,孤僻、懦弱、犹豫不决、迷信、好斗、没有经济头脑、说教、不讲卫生……又无限感慨在这一切弱点之上神一样的力量。米大师一生历经无数战乱、政乱、事业浮沉、流离失所,却七老八十还保存着创造力没有被打垮,大概是因为创作灵感源源不绝——“对于这个美妙的外形的大创造家——同时又是有信仰的人——一个美的躯体是神明般的,是蒙着肉的外衣的神的显示。”
Jun没猜错,米开朗琪罗果然是喜欢男人的。他一生崇拜的偶像是美貌青年卡瓦列里,他叫他“一个有力的天才……一件灵迹……时代的光明”,他又写十四行诗给他,说“我的意志全包括在你的意志中”。这件事就人生和历史来看象一个造物者的玩笑,卡瓦列里有美貌而无才华,米氏有天才而丑陋,结果他激扬了他不世出的杰作。
我对《巨人三传》里米开朗琪罗传腹诽的是,细节少,有很多自相矛盾让人怀疑的地方,不排除为死者讳以及留存资料少(米氏很多十四行诗和书信都遗失了)的原因。但是故事之外,罗曼罗兰在序言里的大声疾呼的确高度概括了我这一年看西画的印象:
“我在此所要叙述的悲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从生命的核心中发出的,它毫无间歇地侵蚀生命,直到把生命完全毁灭为止。这是巨大的人类中最显著的代表之一,一千九百余年来,我们的西方充塞着他的痛苦与信仰的呼声——这代表便是基督徒。
将来,有一天,在多少世纪的终极——如果我们尘世的事迹还能保存于人类记忆中的话——会有一天,那些生存的人们,对于这个消逝的种族,会倚凭在他们堕落的深渊旁边,好似但丁俯在地狱第八层的火坑之旁那样,充满着惊叹、厌恶与怜悯。”
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右走廊里米开朗琪罗的圣母悼子(Pieta)像,比照片小,温润地浸在灯光里。远远地有一种教人心碎的哀伤,透过石材,穿过阻隔游人的玻璃窗,侵入人心。他的创造,生或死,有力或无力,都是一种极致,用以表达这种与生俱来的痛苦,用以抵挡无法捉摸的美的折磨。

他们的绘画数量和质量远不如波盖赛,赫赫有名的埃及馆也不如雅典考古博物馆(更不要提横征暴敛的卢浮宫)。古雕塑如拉奥孔、壁画如拉斐尔画室固然珍贵,毕竟数量有限。如果有什么让梵蒂冈不可取替的,只能是游客争抢立锥之地的西斯廷(Sistine Chapel)。我大步流星挤进这团混乱,登时目瞪口呆。
一面墙的末日审判(The Last Judgment),一团团一摞摞活动的肉体,非常挤逼地zoom in。我把天顶上的上帝创造亚当都给忘光了——那个手势何其温柔,哪有这么风卷狂云式的无穷动。Jun曾说站在西斯廷天顶下,立刻觉得米开朗琪罗是喜欢男人的。看多了印刷版的米式(雄赳赳的)肉体,我也以为自己会是这个感想,没想到站在人海里,那么夺魂摄魄的一刻,竟然感到一种超脱肉体的英雄主义,何其壮烈的人的创造。难以想象和我们一样的肉身凡胎,再寻常不过的颜料画笔,一笔一笔再工整不过的技艺,能泼洒出这么腾空而起、铺天盖地的精神力量,神迹竟出脱于人手。
到这一分钟才明白米开朗琪罗对同时代艺术家如达芬奇、拉斐尔的不屑从何而来。他们如果是顶尖儿大师,米氏可称造物者的信使,使人造如自然,彰显鬼斧神工。
教皇庇护四世令米氏的朋友搞过一个“穿裤子”工程,给末日审判里的裸体画衣服,有树叶、有兽皮。当时的非议者焉知画的是肉体,主旨却在肉体之上呢,譬如众志成城是靠人的力量,没有肉体,哪来精神。他们看到的不过是自己的心罢了。
而米开朗琪罗对绘画竟是不屑的,他最讨厌别人称他画家,他宁愿别人叫他石匠。他毕生的光阴、健康全消耗蹉磨在采石、运石、雕刻、半途而废再重新来过上。末日审判动人的地方,好象是真人变化成雕像,雕像又变化成绘画,憋着全部力量凝结于壁,只需一声号角,就能活生生崩天裂地。是平面的雕塑。
旅途里看傅雷译《巨人三传》,罗曼罗兰不胜惊讶地列举米开朗琪罗的弱点,孤僻、懦弱、犹豫不决、迷信、好斗、没有经济头脑、说教、不讲卫生……又无限感慨在这一切弱点之上神一样的力量。米大师一生历经无数战乱、政乱、事业浮沉、流离失所,却七老八十还保存着创造力没有被打垮,大概是因为创作灵感源源不绝——“对于这个美妙的外形的大创造家——同时又是有信仰的人——一个美的躯体是神明般的,是蒙着肉的外衣的神的显示。”
Jun没猜错,米开朗琪罗果然是喜欢男人的。他一生崇拜的偶像是美貌青年卡瓦列里,他叫他“一个有力的天才……一件灵迹……时代的光明”,他又写十四行诗给他,说“我的意志全包括在你的意志中”。这件事就人生和历史来看象一个造物者的玩笑,卡瓦列里有美貌而无才华,米氏有天才而丑陋,结果他激扬了他不世出的杰作。
我对《巨人三传》里米开朗琪罗传腹诽的是,细节少,有很多自相矛盾让人怀疑的地方,不排除为死者讳以及留存资料少(米氏很多十四行诗和书信都遗失了)的原因。但是故事之外,罗曼罗兰在序言里的大声疾呼的确高度概括了我这一年看西画的印象:
“我在此所要叙述的悲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从生命的核心中发出的,它毫无间歇地侵蚀生命,直到把生命完全毁灭为止。这是巨大的人类中最显著的代表之一,一千九百余年来,我们的西方充塞着他的痛苦与信仰的呼声——这代表便是基督徒。
将来,有一天,在多少世纪的终极——如果我们尘世的事迹还能保存于人类记忆中的话——会有一天,那些生存的人们,对于这个消逝的种族,会倚凭在他们堕落的深渊旁边,好似但丁俯在地狱第八层的火坑之旁那样,充满着惊叹、厌恶与怜悯。”
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右走廊里米开朗琪罗的圣母悼子(Pieta)像,比照片小,温润地浸在灯光里。远远地有一种教人心碎的哀伤,透过石材,穿过阻隔游人的玻璃窗,侵入人心。他的创造,生或死,有力或无力,都是一种极致,用以表达这种与生俱来的痛苦,用以抵挡无法捉摸的美的折磨。

20:55:35 -
barb -
12 January
怎么老是他之卡拉瓦乔
自从“How old are you”被直译成“怎么老是你”之后,Cathayan就曲不离口地借以指摘讽刺我的追星行为。在罗马常常发生的对话是,“咱们到这个地儿是看什么的?”“卡拉瓦乔。”“咱们去那儿干嘛?”“卡拉瓦乔。”“那下一个去哪儿?”……“怎么老是他!”
如果说去马德里是为了格列柯(El Greco),去罗马就是为了卡拉瓦乔(Caravaggio)。看到的计有:
波各赛美术馆(Galleria Borghese)六幅
San Luigi dei Francesi教堂三幅
巴贝里尼宫(Palazzo Barberini)两幅
多利亚潘菲美术馆(Galleria Doria Pamphilj)两幅
San Agostino教堂一幅
梵蒂冈博物馆(Vaticana)一幅
卡比托奈博物馆(Capitolini)一幅
外加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Uffizi)一幅。就这样还漏掉不少,罗马波波洛广场(Popolo)的圣玛丽亚教堂有两幅未来得及看,乌菲兹的两幅又被借到皮蒂宫(Pitti)搞临展,C同学忙着看主显节游行的热闹,我又差点被佛罗伦萨的阴风吹得病倒,遂悻悻而归。
前几天看迈克专栏写去马耳他,把看一幅卡拉瓦乔当大节目,似乎迢迢去途的奖赏,我完全能理解。在卢浮宫密密麻麻的宝物里,虽然格列柯印象最深,第一眼认出的画家却是卡拉瓦乔,好象陌生世界突然辨出一个间接的朋友,不熟也有三分亲。
这回看到的虽然不乏美杜莎(Medusa)、果篮少年(boy with a basket of fruit)这样的神作,我却有点偏心巴贝里尼宫的纳希瑟斯(Narcissus)。水仙花少年按说是要很美才到顾影自怜的地步,可是河边这位少年气色不佳,有抬头纹,青春在去留之间——那痴迷的目光,早穿透了皮相,是自己在拥抱自己,一寸寸从里到外掰开来揉碎了地描摹爱慕。卡拉瓦乔哪一幅画没有这个精神?:wink:
格列柯是千人一面,对着哪幅画哪个人物都好象对着他自己,同一副精神面貌。卡拉瓦乔是游荡在他的画里,这里挤一下眉,那里弄一下眼,戏蝶一样。你以为他是游戏风尘,却每个细节禁得起严苛的考究。近看是果皮上的虫子洞,远看是暗黑中的一簇光,远观亵玩两可。
他最为人称道的不是肉身少年、烂熟水果和血溅三尺吗,这次竟觉得他的教堂画也好。印刷品上看稀松平常的,搁在最日常不过实实在在的环境里(而不是供奉于殿堂),在幽微的光线下自有明灭,还有一般宗教画鲜有的活泼的戏剧感,象往世的录像重播。比较好玩的是教堂中午关门,半下午才重开,门前坐满人,我以为是虔诚的本地教徒等着做礼拜,结果一开门就蜂涌到卡拉瓦乔座前——原来都是信徒。
波各赛藏的卡拉瓦乔比起别的美术馆简直是丰饶之海——一幅裸身少年圣约翰(St John the Baptist)、一幅伪托酒神的放荡自画像(Bacchus)、一幅果篮少年、一幅踩蛇的婴儿(Madonna dei Palafrenieri)、一幅老者与骷髅头(St Jerome)、一幅少年大卫王砍掉巨人头(David with the Head of Goliath),基本上集结了卡拉瓦乔全线产品,挂在小房间的两面墙上。正好我走错路,逆流而行先进了这本该最后到的房间,一个人静静看了个饱。
多利亚潘菲美术馆的两幅则象飞来横财。地方冷僻,却一副末世贵族派头,许多名家作品累累赘赘挂在寂寞的镜厅一侧,任你改朝换代我自岿然不动。两幅都不是典型的卡拉瓦乔,不嚣张,不戏剧化,但卡拉瓦乔也不是生下来就这么卡拉瓦乔的嘛(我多想看看不那么博斯的博斯,不那么夏加尔的夏加尔啊)。
最后叨叨一下最大的遗憾——佛罗伦萨的皮蒂宫自存的大婴儿像,Sleeping Cupid。过门而不入,就当是给自己留个借口旧地重游吧。

Narcissus - 巴贝里尼宫

St John the Baptist - 波各赛

Bacchus - 波各赛

Boy with A Basket of Fruit - 波各赛

Madonna dei Palafrenieri - 波各赛

Judith Beheading Bolofernes - 巴贝里尼宫

San Luigi dei Francesi教堂

Sleeping Cupid - 皮蒂宫
如果说去马德里是为了格列柯(El Greco),去罗马就是为了卡拉瓦乔(Caravaggio)。看到的计有:
波各赛美术馆(Galleria Borghese)六幅
San Luigi dei Francesi教堂三幅
巴贝里尼宫(Palazzo Barberini)两幅
多利亚潘菲美术馆(Galleria Doria Pamphilj)两幅
San Agostino教堂一幅
梵蒂冈博物馆(Vaticana)一幅
卡比托奈博物馆(Capitolini)一幅
外加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Uffizi)一幅。就这样还漏掉不少,罗马波波洛广场(Popolo)的圣玛丽亚教堂有两幅未来得及看,乌菲兹的两幅又被借到皮蒂宫(Pitti)搞临展,C同学忙着看主显节游行的热闹,我又差点被佛罗伦萨的阴风吹得病倒,遂悻悻而归。
前几天看迈克专栏写去马耳他,把看一幅卡拉瓦乔当大节目,似乎迢迢去途的奖赏,我完全能理解。在卢浮宫密密麻麻的宝物里,虽然格列柯印象最深,第一眼认出的画家却是卡拉瓦乔,好象陌生世界突然辨出一个间接的朋友,不熟也有三分亲。
这回看到的虽然不乏美杜莎(Medusa)、果篮少年(boy with a basket of fruit)这样的神作,我却有点偏心巴贝里尼宫的纳希瑟斯(Narcissus)。水仙花少年按说是要很美才到顾影自怜的地步,可是河边这位少年气色不佳,有抬头纹,青春在去留之间——那痴迷的目光,早穿透了皮相,是自己在拥抱自己,一寸寸从里到外掰开来揉碎了地描摹爱慕。卡拉瓦乔哪一幅画没有这个精神?:wink:
格列柯是千人一面,对着哪幅画哪个人物都好象对着他自己,同一副精神面貌。卡拉瓦乔是游荡在他的画里,这里挤一下眉,那里弄一下眼,戏蝶一样。你以为他是游戏风尘,却每个细节禁得起严苛的考究。近看是果皮上的虫子洞,远看是暗黑中的一簇光,远观亵玩两可。
他最为人称道的不是肉身少年、烂熟水果和血溅三尺吗,这次竟觉得他的教堂画也好。印刷品上看稀松平常的,搁在最日常不过实实在在的环境里(而不是供奉于殿堂),在幽微的光线下自有明灭,还有一般宗教画鲜有的活泼的戏剧感,象往世的录像重播。比较好玩的是教堂中午关门,半下午才重开,门前坐满人,我以为是虔诚的本地教徒等着做礼拜,结果一开门就蜂涌到卡拉瓦乔座前——原来都是信徒。
波各赛藏的卡拉瓦乔比起别的美术馆简直是丰饶之海——一幅裸身少年圣约翰(St John the Baptist)、一幅伪托酒神的放荡自画像(Bacchus)、一幅果篮少年、一幅踩蛇的婴儿(Madonna dei Palafrenieri)、一幅老者与骷髅头(St Jerome)、一幅少年大卫王砍掉巨人头(David with the Head of Goliath),基本上集结了卡拉瓦乔全线产品,挂在小房间的两面墙上。正好我走错路,逆流而行先进了这本该最后到的房间,一个人静静看了个饱。
多利亚潘菲美术馆的两幅则象飞来横财。地方冷僻,却一副末世贵族派头,许多名家作品累累赘赘挂在寂寞的镜厅一侧,任你改朝换代我自岿然不动。两幅都不是典型的卡拉瓦乔,不嚣张,不戏剧化,但卡拉瓦乔也不是生下来就这么卡拉瓦乔的嘛(我多想看看不那么博斯的博斯,不那么夏加尔的夏加尔啊)。
最后叨叨一下最大的遗憾——佛罗伦萨的皮蒂宫自存的大婴儿像,Sleeping Cupid。过门而不入,就当是给自己留个借口旧地重游吧。

Narcissus - 巴贝里尼宫

St John the Baptist - 波各赛

Bacchus - 波各赛

Boy with A Basket of Fruit - 波各赛

Madonna dei Palafrenieri - 波各赛

Judith Beheading Bolofernes - 巴贝里尼宫

San Luigi dei Francesi教堂

Sleeping Cupid - 皮蒂宫
22:01:59 -
barb -
08 January
辞旧迎新
年底的时候陷入没日历用的焦虑。倒不是数着日子过,还是因为记性不好,喜欢把休假日期、重要事件什么的写在挂历上,便于来回翻看。因为是每天看的东西,自然想看些赏心悦目喜闻乐见的,去年的三本就很中意,一本是斯图加特芭蕾舞团的黑白图片,记得当时搞了两本,一本给小山一本自用;一本是f 先生给的希腊景色和食谱,一年下来希腊菜除了橄榄油拌沙拉什么都没学会,倒是爱琴海的蓝与白看了个通透;还有一本好象也是从f 先生那儿剥削的GQ附送台历,都是GQ的帅哥美女封面(我专门看中了Daniel Craig那页),可惜日历和图是正反两面,台历搁在窗台上(我们住一楼),帅哥美女都便宜了窗外过路的。
圣诞节休假的时候特地在马尔默书店搜寻一番,除了小动物、斯科讷风景和大公主维多利亚及其健身教练老公丹尼尔外没有别的选择(瑞典显然没有送挂历的文化),回来信誓旦旦地说,去罗马别的不说,好歹得搞两本好挂历!昨天晚上从罗马回来,扔下背包第一件事是把新挂历拿出来挂上,有一种去罗马是为了买挂历的错觉……
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挂历很游客化,不是废墟,就是名画,梵帝冈博物馆就卖西斯廷,波各赛美术馆就卖贝尼尼和卡拉瓦乔,乌菲兹美术馆就卖波提切利,学院美术馆就卖大卫。最后终于在罗马中央车站(Termini)看到teNeues的挂历系列,一见钟情。他们的艺术系列从文艺复兴到当代艺术都有,从席勒(Egon Schiele)到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从凯斯哈灵(Keith Haring)到安藤广重(Ando Hiroshige),略风格化的好象都有了,甚至还有Paul Frank的大嘴猴。我一开始在两本霍珀(Edward Hopper)中间犹豫,又始终觉得他的调子太清冷,不利于防止瑞典的冬季抑郁症,突然看到另一本一个不熟悉的画家Jack Vettriano,比霍珀暧昧,不乏火辣的男女调情场景,却有一种和霍珀相仿的孤寂,也有类似的宣传画(比如Mad Men式的广告)、电影场景和雷蒙钱德勒式孤胆英雄的调调。好吧,就来个陌生人吧,防止审美疲劳。
搜索了一下,Jack Vettriano是个自学成才的苏格兰人,原本是工程师,默默作画十数年,不知怎么突然得到评论认可,大开展览——在知道他是苏格兰人之前,我一看他画里的场景马上先想到苏格兰芭蕾舞团的一场舞Pennies from Heaven,也是同样的时代风格和红男绿女,难道苏格兰人特别喜欢这个?

我买的是这一本


原来他们零六年就出过Vettriano系列







这估计是Jack Vettriano年轻的时候
圣诞节休假的时候特地在马尔默书店搜寻一番,除了小动物、斯科讷风景和大公主维多利亚及其健身教练老公丹尼尔外没有别的选择(瑞典显然没有送挂历的文化),回来信誓旦旦地说,去罗马别的不说,好歹得搞两本好挂历!昨天晚上从罗马回来,扔下背包第一件事是把新挂历拿出来挂上,有一种去罗马是为了买挂历的错觉……
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挂历很游客化,不是废墟,就是名画,梵帝冈博物馆就卖西斯廷,波各赛美术馆就卖贝尼尼和卡拉瓦乔,乌菲兹美术馆就卖波提切利,学院美术馆就卖大卫。最后终于在罗马中央车站(Termini)看到teNeues的挂历系列,一见钟情。他们的艺术系列从文艺复兴到当代艺术都有,从席勒(Egon Schiele)到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从凯斯哈灵(Keith Haring)到安藤广重(Ando Hiroshige),略风格化的好象都有了,甚至还有Paul Frank的大嘴猴。我一开始在两本霍珀(Edward Hopper)中间犹豫,又始终觉得他的调子太清冷,不利于防止瑞典的冬季抑郁症,突然看到另一本一个不熟悉的画家Jack Vettriano,比霍珀暧昧,不乏火辣的男女调情场景,却有一种和霍珀相仿的孤寂,也有类似的宣传画(比如Mad Men式的广告)、电影场景和雷蒙钱德勒式孤胆英雄的调调。好吧,就来个陌生人吧,防止审美疲劳。
搜索了一下,Jack Vettriano是个自学成才的苏格兰人,原本是工程师,默默作画十数年,不知怎么突然得到评论认可,大开展览——在知道他是苏格兰人之前,我一看他画里的场景马上先想到苏格兰芭蕾舞团的一场舞Pennies from Heaven,也是同样的时代风格和红男绿女,难道苏格兰人特别喜欢这个?

我买的是这一本


原来他们零六年就出过Vettriano系列







这估计是Jack Vettriano年轻的时候
10:18:11 -
bar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