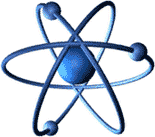Jump to navigation
Barb的不老歌
02 June
早晨
新同事问我,为何坐八点五分的班车,却要六点半起床。我想了半天,只好说,我磨蹭。确实,六点半闹钟叫,我先按熄了它,闭着眼痛苦地挣扎十分钟,再爬起来,走到客厅喝水,然后躺在窗下的沙发十分钟,发呆或看报纸(外滩画报较适合此情境,字多就不行),然后吃早点。最近因为姥姥在我家,Cathayan每天早上都很勤快地买豆浆油条包子,我得以沾光,边吃边看电视。然后收拾洗漱,然后几乎从不例外地,跳着脚冲出家门,蹿上电梯,疾走至大门口,明明准备乘公车的,零钱都揣在袋里,却不得已地打了车,差一分钟都会乘不上班车。
忙碌的生活,晚上就不去说它,回到家没走什么过场就呼呼大睡。并且呼呼大睡已是较好结局,Cathayan对此表示诧异,因为我通常换新工作都是睡不着觉,或是没觉可睡。于是一整个星期里,自我就被挤逼成了早上那一小点儿。由此可见恶习常常都有某种心理需求做硬实后盾,同时兼任安慰剂,不由人想戒就戒。
离开上一份工作,老板们请吃饭时,聊到部门老板的日本太太天天起大早给家人准备丰盛的早餐(米饭、自制汉堡……),我们的实习生说,韩剧里常常看到韩国人一早就吃米饭、酱汤,和一桌子的菜。不知社会进步,工业进步,这种早晨的习惯是否可以长久保留。
广东人道早安,有时说是“早晨”。我特别喜欢听,觉得简朴而亲切。广东人的早茶,洋洋洒洒,可以到中午,简直奢侈。我记得有个周末的早晨,我病了,醒得早,和爸爸妈妈去雍和宫旁的金鼎轩吃早点,点了粥、斋肠粉、云吞面……干疼的喉咙顿时滋润。北方人晏起,稍微早一点,即觉环境清净,时间充裕,并且纯是拿来享用的。
阮玲玉是贪点儿依赖,贪一点儿爱,我是贪点儿早晨,贪一点儿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