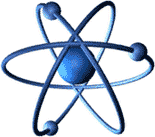Barb的不老歌
31 July
日内瓦
把日内瓦当成中转站,短暂停留,仍然对它的老城和湖有印象。
城市乍一看乱糟糟,大吊车无处不在,后来发现是瑞士的普遍现象,山间小镇也不例外,不遗余力拉动经济。老房子也有很多在维修,搭着脚手架。一些老楼布满花纹,别致繁屑的露台让人想起在巴塞罗那看到的西班牙建筑师多米尼克蒙特内(Domènech i Montaner)的作品。我进去楼底的饼店买面包,又用上了在巴黎学到的法语三板斧,“蹦猪”(bonjour)、“没洗”(Merci)和“偶喝哇喝”(Au revoir)。
走了一些小街,地势高低起伏,花盆里种着芭蕉,街角有蔬果摊,一时觉得到了中国南方小城,只是定睛一看价格,幻觉立刻消失:mrgreen: 小饭馆标价一道菜三四十法郎(兑人民币和瑞典克朗是一比八左右),我们匆匆逃往超市。喝到了无比美味的瑞士牛奶,感觉比瑞典的还要好喝很多。
日内瓦湖边真切感觉到该城的国际化,不只各种肤色种族的人群,而且很多穿着各国服装,姿态各异,享受同一面湖水和晚风。跟着本地人把吃剩的面包喂了湖里的天鹅鸭子,它们一拥而上,追讨不休。天鹅摇头摆尾,在水里追着人乞食,象小狗一样。和鸭子抢食物时,又变成骜犬:P 这面大湖绵延到洛桑,似乎是我见过最大的湖泊。



在日内瓦美术馆附近看到这样一座庙,多少有点惊讶。它的金光闪烁,和富庶但是低调的日内瓦人风格迥异。
马尔默也有很多中东移民,但鲜少见到如日内瓦出入豪华酒店、黑袍下名牌累累、成群结队的阿拉伯美少妇。

从桌布到裙子,一水儿白色

街角。西红柿八块九法郎。


城市乍一看乱糟糟,大吊车无处不在,后来发现是瑞士的普遍现象,山间小镇也不例外,不遗余力拉动经济。老房子也有很多在维修,搭着脚手架。一些老楼布满花纹,别致繁屑的露台让人想起在巴塞罗那看到的西班牙建筑师多米尼克蒙特内(Domènech i Montaner)的作品。我进去楼底的饼店买面包,又用上了在巴黎学到的法语三板斧,“蹦猪”(bonjour)、“没洗”(Merci)和“偶喝哇喝”(Au revoir)。
走了一些小街,地势高低起伏,花盆里种着芭蕉,街角有蔬果摊,一时觉得到了中国南方小城,只是定睛一看价格,幻觉立刻消失:mrgreen: 小饭馆标价一道菜三四十法郎(兑人民币和瑞典克朗是一比八左右),我们匆匆逃往超市。喝到了无比美味的瑞士牛奶,感觉比瑞典的还要好喝很多。
日内瓦湖边真切感觉到该城的国际化,不只各种肤色种族的人群,而且很多穿着各国服装,姿态各异,享受同一面湖水和晚风。跟着本地人把吃剩的面包喂了湖里的天鹅鸭子,它们一拥而上,追讨不休。天鹅摇头摆尾,在水里追着人乞食,象小狗一样。和鸭子抢食物时,又变成骜犬:P 这面大湖绵延到洛桑,似乎是我见过最大的湖泊。



在日内瓦美术馆附近看到这样一座庙,多少有点惊讶。它的金光闪烁,和富庶但是低调的日内瓦人风格迥异。
马尔默也有很多中东移民,但鲜少见到如日内瓦出入豪华酒店、黑袍下名牌累累、成群结队的阿拉伯美少妇。

从桌布到裙子,一水儿白色

街角。西红柿八块九法郎。


13:35:57 -
barb -
30 July
人在旅途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出门常常想起“人在旅途”四个字,以前有出老新加坡电视剧叫这个名字,主题歌的旋律犹在耳边,直白的歌词却记不得了。
因为或许是两年内最后一旅,所以特别珍惜,虽然顾及体力,还是把行程塞得满满的。
第一站日内瓦,因为从哥本哈根飞到瑞士的廉航只找到这个目的地。在日内瓦住了一夜,坐火车直上苏黎世,参观慕名已久的苏黎世美术馆——这回因为体力的关系,削减博物馆和美术馆参观,虽然可惜,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和在该城读书的豚豚世弟见面,一起游荡老城。次日坐车到卢塞恩(Lucern),阴雨濛濛里游廊桥。下一天坐卢塞恩至因特拉肯的“黄金线(Golden Pass)”列车见识瑞士的湖光山色,中间在豚豚强烈推荐的小镇Brienz下车散步。再从因特拉肯乘车往伯尔尼,从伯尔尼经洛桑返回日内瓦。
在瑞士唯一的遗憾是因为时间和体力没能去巴塞尔看瑞士最好的美术馆和全世界藏量最多的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的画,希望日后有机会能和德国联成一旅。
二十日上午从日内瓦飞回哥本哈根,晚上飞挪威的卑尔根(Bergen)。因为中间有六七个小时等待时间,又惦记家里的花,干脆回到马尔默。结果一看在C同学的布条浇花法(把布条一头放在水盆里,另一头塞在花盆土里,花会自己汲取水分)的照顾下,最需要水的花都安然无恙。

晚上到卑尔根,第二天在老城漫游,逛市场和吃鱼。第三天清晨按之前选好的“Norway in a Nutshell”的路线,先乘船游览挪威峡湾中最长最深的松恩峡湾(Sognefjord),在小城弗洛姆(Flåm)上岸,转搭火车一路登山到Mydal,从那里换车至奥斯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路阴雨,峡湾固然壮美,山间景色却总觉得比不上瑞士的神仙小镇。
到奥斯陆的时候,震惊世界的爆炸和小岛杀戮刚刚发生。我们也很震惊,犹豫了一晚上,决定行程照旧。但在奥斯陆自然游兴缺缺,因此基本是默默旁观事件发生后的城市。
二十四日飞往赫尔辛基,耳目一新,不管从城市、语言、文化……各方面看,这个国度都是最不北欧的地方,因为那些老旧的俄式建筑,反而有一点点亲切感。中间去图尔库(Turku)玩了一天,f告诉我它今年是“欧洲文化之都”,我们去纯属好奇这个瑞典人去芬兰最频繁的地方(图尔库和斯德哥尔摩之间有海航)有啥特别,事实杀死了好奇心。在赫尔辛基再游一天,打道回府,虽然恋恋不舍,也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我慢慢把照片放上来。
因为或许是两年内最后一旅,所以特别珍惜,虽然顾及体力,还是把行程塞得满满的。
第一站日内瓦,因为从哥本哈根飞到瑞士的廉航只找到这个目的地。在日内瓦住了一夜,坐火车直上苏黎世,参观慕名已久的苏黎世美术馆——这回因为体力的关系,削减博物馆和美术馆参观,虽然可惜,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和在该城读书的豚豚世弟见面,一起游荡老城。次日坐车到卢塞恩(Lucern),阴雨濛濛里游廊桥。下一天坐卢塞恩至因特拉肯的“黄金线(Golden Pass)”列车见识瑞士的湖光山色,中间在豚豚强烈推荐的小镇Brienz下车散步。再从因特拉肯乘车往伯尔尼,从伯尔尼经洛桑返回日内瓦。
在瑞士唯一的遗憾是因为时间和体力没能去巴塞尔看瑞士最好的美术馆和全世界藏量最多的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的画,希望日后有机会能和德国联成一旅。
二十日上午从日内瓦飞回哥本哈根,晚上飞挪威的卑尔根(Bergen)。因为中间有六七个小时等待时间,又惦记家里的花,干脆回到马尔默。结果一看在C同学的布条浇花法(把布条一头放在水盆里,另一头塞在花盆土里,花会自己汲取水分)的照顾下,最需要水的花都安然无恙。

晚上到卑尔根,第二天在老城漫游,逛市场和吃鱼。第三天清晨按之前选好的“Norway in a Nutshell”的路线,先乘船游览挪威峡湾中最长最深的松恩峡湾(Sognefjord),在小城弗洛姆(Flåm)上岸,转搭火车一路登山到Mydal,从那里换车至奥斯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路阴雨,峡湾固然壮美,山间景色却总觉得比不上瑞士的神仙小镇。
到奥斯陆的时候,震惊世界的爆炸和小岛杀戮刚刚发生。我们也很震惊,犹豫了一晚上,决定行程照旧。但在奥斯陆自然游兴缺缺,因此基本是默默旁观事件发生后的城市。
二十四日飞往赫尔辛基,耳目一新,不管从城市、语言、文化……各方面看,这个国度都是最不北欧的地方,因为那些老旧的俄式建筑,反而有一点点亲切感。中间去图尔库(Turku)玩了一天,f告诉我它今年是“欧洲文化之都”,我们去纯属好奇这个瑞典人去芬兰最频繁的地方(图尔库和斯德哥尔摩之间有海航)有啥特别,事实杀死了好奇心。在赫尔辛基再游一天,打道回府,虽然恋恋不舍,也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我慢慢把照片放上来。
10:42:41 -
barb -
14 July
珍宝
新居网弄好后多半在围脖打混,那里消息快图片多,让我这个极不灵通人士常有眼花缭乱之感(虽然也挺浪费时间)。这几天看到一个(或一群?)叫“中国书画艺术”的贴出文徵明的字《草堂十志》一幅以及朗世宁的花鸟画,勾起很多回忆。一是少时看叔叔写字,被追着叫好:mrgreen: 二是少读金庸小说,偶尔看到郎世宁所作香妃像,非常吸引。那幅工笔小像用色大胆,显是西洋画影响。
刚好翻看借Junshan的毛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 1922),有一章叫《内阁部长》(按年头应该不难查到此人是谁,就是懒得去查),哎,真好看——原来毛姆有福见到若干真迹。这位部长是个大收藏家,逐一给他展示唐三彩、书、画,还讲起逸闻趣事。毛姆写道观感:
“那是一系列小张的花鸟画,虽只寥寥数笔,却栩栩如生,它们有着多么丰富的联想、多么伟大的自然情感和多么动人的温柔,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几根嫩枝,开出点点梅花,就包含了春天所有鲜活的魅力;几只小鸟,惊起根根羽毛,便表现出生命中的博动和战栗。这是一个艺术大师的杰作。”
“动人的温柔”说得极好,真想知道画家是谁。
但是呢,毛姆就是毛姆,你正在想他怎么离开人性这个老焦点咏起物来,果然笔锋一转,进入高潮:
“但对我而言,这次见面中最奇妙的事情是,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根本就是个恶棍,腐败渎职、寡廉鲜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是一个搜刮的高手,通过极其恶劣的手段掠夺了大量财富。他是个虚伪、残忍、报复心强、行贿受贿的人,中国沦落到他所悲叹的这个地步,他本人也难辞其咎。然而,当他拿起一只天青色小花瓶时,他的手指微曲,带着一种迷人的温情,忧郁的目光仿佛在轻轻地抚摸,他的双唇微微张开,似乎发出一声充满欲望的叹息。”
所以我们看艺术作品的时候,不敢追问赵孟頫、赵佶、高更……是谁。

文徵明《草堂十志》第一幅(我立刻设为桌面)

郎世宁《黄刺么与鱼儿牡丹》,感觉像西画多过国画
刚好翻看借Junshan的毛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 1922),有一章叫《内阁部长》(按年头应该不难查到此人是谁,就是懒得去查),哎,真好看——原来毛姆有福见到若干真迹。这位部长是个大收藏家,逐一给他展示唐三彩、书、画,还讲起逸闻趣事。毛姆写道观感:
“那是一系列小张的花鸟画,虽只寥寥数笔,却栩栩如生,它们有着多么丰富的联想、多么伟大的自然情感和多么动人的温柔,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几根嫩枝,开出点点梅花,就包含了春天所有鲜活的魅力;几只小鸟,惊起根根羽毛,便表现出生命中的博动和战栗。这是一个艺术大师的杰作。”
“动人的温柔”说得极好,真想知道画家是谁。
但是呢,毛姆就是毛姆,你正在想他怎么离开人性这个老焦点咏起物来,果然笔锋一转,进入高潮:
“但对我而言,这次见面中最奇妙的事情是,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根本就是个恶棍,腐败渎职、寡廉鲜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是一个搜刮的高手,通过极其恶劣的手段掠夺了大量财富。他是个虚伪、残忍、报复心强、行贿受贿的人,中国沦落到他所悲叹的这个地步,他本人也难辞其咎。然而,当他拿起一只天青色小花瓶时,他的手指微曲,带着一种迷人的温情,忧郁的目光仿佛在轻轻地抚摸,他的双唇微微张开,似乎发出一声充满欲望的叹息。”
所以我们看艺术作品的时候,不敢追问赵孟頫、赵佶、高更……是谁。

文徵明《草堂十志》第一幅(我立刻设为桌面)

郎世宁《黄刺么与鱼儿牡丹》,感觉像西画多过国画
07:42:30 -
barb -
13 July
食用鸽
搬家的过程中发掘出一批带过来一直没功夫没看的零九年的旧杂志报纸,忙里偷闲地看起来。这一本《明日风尚》的副刊,是王世襄去世的纪念专辑,有一些亲友后辈的文章和照片,还有对话录。对话录里这一段特别逗:
“我觉得最大的危机是,许多年轻人没有传统文化的底子,不认好坏。我举个例子——鸽子,中国的鸽子有几百年的传统,在明朝就写了专书《鸽经》,在全世界是最早的一部鸽书,记录了多少种几百年来精心培养出来的好品种,在世界上是最美丽的,可是我们的好鸽子要绝种了。为什么要绝种了呢?因为养的人少了,养的人少了跟人的生活有关系,都搬到楼房去住,没有院子了,没法养鸽子了。那么多楼,鸽子也没法飞了,好鸽子少了,人们就不知道中国传统鸽子是什么样子了。我举个例子吧,中央电视台一台《东方时空》,看升旗,放鸽子,一个白鸽子飞过来,大长嘴,这鸽子是美国的食用鸽,最难看的。你说中央第一套节目,用一个美国食用鸽,真是伤我的自尊心哪!很多歌星啊,唱完歌把手中的鸽子一放,这鸽子还是食用鸽。上海人民广场的广场鸽,都是鸽场来的食用鸽,他们就是目中没有中国的传统观赏鸽。”
这话说不出的遗老遗少气——翻看王的家世,高祖历任几省巡抚、总督和工部尚书;祖父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伯祖是光绪年状元,任镇江、苏州知府;父为著名外交官,母为著名鱼藻画家。他的书(以明代家具专著传世,兼及漆器、竹刻、国画、古乐、鸽哨、葫芦、蟋蟀、金鱼……等等)我没看过,想看来着,但是没有那样的心境——别看他也吃过苦(文革),要童年有很宽裕的环境,才养的出那份闲散心和“玩物丧志”的安全感。他叹息人心不古,有一句话说对了,环境变了,不允许了。余光中说的好,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如何再送她一首菩萨蛮?
有些传统文化就是要消逝,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有心人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社会变迁,排沙见金,全靠它自己有多大的民间底子。旧的消逝了有新的来补,我看英国画家David Hockney拿iPad做的画就比他的传统画好看有趣。
其实我觉得食用鸽还挺Q的……以前CY去加拿大学校交换访问的时候,说起房东刻薄,四川男同事老吃不饱,饿得眼睛盯着池塘里的鸭子放光……食用鸽说不定有画饼充饥的疗效:mrgreen: 马尔默大街上的胖鸽子,长得也不怎么样,但是走来走去吃吃别人丢的干面包,是群活泼的小动物,也挺喜人。
黄苗子说中国人是学巴黎啊英国的什么广场放很多鸽子,王世襄说,“他们的鸽子并不好,都是野鸽子,很讨厌,传染病啊,拉屎啊,因为它不是好好地管起来养的,和家养鸽子不是一回事。” 传染病这事是有的,小时候养过鸽子的C同学观察了一下,意大利法国的鸽子都烂脚,好像没有传到北欧,不记得北京上海有没有。
“我觉得最大的危机是,许多年轻人没有传统文化的底子,不认好坏。我举个例子——鸽子,中国的鸽子有几百年的传统,在明朝就写了专书《鸽经》,在全世界是最早的一部鸽书,记录了多少种几百年来精心培养出来的好品种,在世界上是最美丽的,可是我们的好鸽子要绝种了。为什么要绝种了呢?因为养的人少了,养的人少了跟人的生活有关系,都搬到楼房去住,没有院子了,没法养鸽子了。那么多楼,鸽子也没法飞了,好鸽子少了,人们就不知道中国传统鸽子是什么样子了。我举个例子吧,中央电视台一台《东方时空》,看升旗,放鸽子,一个白鸽子飞过来,大长嘴,这鸽子是美国的食用鸽,最难看的。你说中央第一套节目,用一个美国食用鸽,真是伤我的自尊心哪!很多歌星啊,唱完歌把手中的鸽子一放,这鸽子还是食用鸽。上海人民广场的广场鸽,都是鸽场来的食用鸽,他们就是目中没有中国的传统观赏鸽。”
这话说不出的遗老遗少气——翻看王的家世,高祖历任几省巡抚、总督和工部尚书;祖父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伯祖是光绪年状元,任镇江、苏州知府;父为著名外交官,母为著名鱼藻画家。他的书(以明代家具专著传世,兼及漆器、竹刻、国画、古乐、鸽哨、葫芦、蟋蟀、金鱼……等等)我没看过,想看来着,但是没有那样的心境——别看他也吃过苦(文革),要童年有很宽裕的环境,才养的出那份闲散心和“玩物丧志”的安全感。他叹息人心不古,有一句话说对了,环境变了,不允许了。余光中说的好,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如何再送她一首菩萨蛮?
有些传统文化就是要消逝,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有心人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社会变迁,排沙见金,全靠它自己有多大的民间底子。旧的消逝了有新的来补,我看英国画家David Hockney拿iPad做的画就比他的传统画好看有趣。
其实我觉得食用鸽还挺Q的……以前CY去加拿大学校交换访问的时候,说起房东刻薄,四川男同事老吃不饱,饿得眼睛盯着池塘里的鸭子放光……食用鸽说不定有画饼充饥的疗效:mrgreen: 马尔默大街上的胖鸽子,长得也不怎么样,但是走来走去吃吃别人丢的干面包,是群活泼的小动物,也挺喜人。
黄苗子说中国人是学巴黎啊英国的什么广场放很多鸽子,王世襄说,“他们的鸽子并不好,都是野鸽子,很讨厌,传染病啊,拉屎啊,因为它不是好好地管起来养的,和家养鸽子不是一回事。” 传染病这事是有的,小时候养过鸽子的C同学观察了一下,意大利法国的鸽子都烂脚,好像没有传到北欧,不记得北京上海有没有。
08:26:13 -
bar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