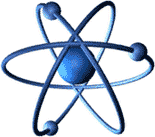Barb的不老歌
25 April
倦
小时候看香港电视剧,喜欢江华脸上淡淡的倦意。他貌不出众,能熬成男主角,总要有些特别的东西,我想是那股懒洋洋的气质。可见我从小不是个积极乐观的孩子。
爱看勒卡雷,也多半为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倦怠:一些普通人间谍们,有着普通人的焦虑和无奈,活计还得干下去,身不由己。我很喜欢他在第一本书《电话疑云》(Call for the Dead)里的序,他说“我开始写作是由于对生活厌烦得要发疯了”。据说他自己是个怪老头儿,七老八十了,独自住在悬崖上的房子里,厌恶人群。能吸引他小说里人物的,也尽是一些怪人,多数受尽折磨,要么是饥饿,要么是战争,要么是拷打逼供。好在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不会让人读得不舒服。
要说多么喜欢间谍题材,未必。吸引我的是那调调,按部就班的,普通人的,被时代的洪流席卷着,淘汰着。最爱的当然是小头头乔治史迈利(Smiley),他是个五短身材的胖老头,性格文静。我本以为他应该具有惊人坚毅的性格,是块处变不惊的老姜,却意外地看到他的愤怒、无奈、脆弱……这些日常的感情,甭管他处理多么大的阴谋。
《电话疑云》里,“突然间,他感受到一种经受不住挫折的惊恐在内心里升腾起来。随着惊恐而来的,是对这个满头灰发、满脸理智笑容的装腔作势的马屁精、猥亵的娘娘腔的无法抑制的愤怒。惊恐与愤怒随着一股突然而至的潮水往上涌来,弥漫他的全身。他感到脸火辣辣的,镜片变得模糊了,陡然间眼泪汪汪的,平添了他的羞辱。”对面那个人是他的新上司。
春天不是读书天。前几个周末宁愿去看花,在一场毛毛雨后赶上了元大都遗址公园的白海棠,又特地绕远坐地铁看了两次大钟寺站旁边开得密不成样的桃花。书就一直搁着。拜大风天所赐,终于看完了延宕好久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我本来记性就不好,勒卡雷的小说又人物众多,时间拖得一长,就老是忘了前情。难怪他的书都要有人物表,我特地折起那一页,新出场一个人就翻回去看,到底谁是“剥头皮组”的,谁是“点路灯组”的。中间有点不耐烦,几乎迷失了,结果一到结尾,并不是恍然大悟,反而是一种反高潮的黯然神伤。我也挺莫名其妙:他并没抛出什么重量级的煽情手榴弹,怎么我就感伤了。大概是开头和结尾密密衔接了起来,那种最普通的小男孩的眼睛所看到普通的一幕,衬托着那个既不是主角也不是英雄的前特工惊人的过去,而他也不过是为了衬托史迈利挖出来的内鬼,那君子人儿的悲剧性。
还有安,史迈利的太太,也是他永远得不到的女人,像个鬼魂儿一样氤氲在他孤零零的生活里。加重了这种愁苦的气氛。
真见鬼,我本来读的是所谓的硬汉小说,一个是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一个是《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没想到一个比一个弯,一个比一个酸的馒头(sentimental)!看得我又爱又恨。
爱看勒卡雷,也多半为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倦怠:一些普通人间谍们,有着普通人的焦虑和无奈,活计还得干下去,身不由己。我很喜欢他在第一本书《电话疑云》(Call for the Dead)里的序,他说“我开始写作是由于对生活厌烦得要发疯了”。据说他自己是个怪老头儿,七老八十了,独自住在悬崖上的房子里,厌恶人群。能吸引他小说里人物的,也尽是一些怪人,多数受尽折磨,要么是饥饿,要么是战争,要么是拷打逼供。好在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不会让人读得不舒服。
要说多么喜欢间谍题材,未必。吸引我的是那调调,按部就班的,普通人的,被时代的洪流席卷着,淘汰着。最爱的当然是小头头乔治史迈利(Smiley),他是个五短身材的胖老头,性格文静。我本以为他应该具有惊人坚毅的性格,是块处变不惊的老姜,却意外地看到他的愤怒、无奈、脆弱……这些日常的感情,甭管他处理多么大的阴谋。
《电话疑云》里,“突然间,他感受到一种经受不住挫折的惊恐在内心里升腾起来。随着惊恐而来的,是对这个满头灰发、满脸理智笑容的装腔作势的马屁精、猥亵的娘娘腔的无法抑制的愤怒。惊恐与愤怒随着一股突然而至的潮水往上涌来,弥漫他的全身。他感到脸火辣辣的,镜片变得模糊了,陡然间眼泪汪汪的,平添了他的羞辱。”对面那个人是他的新上司。
春天不是读书天。前几个周末宁愿去看花,在一场毛毛雨后赶上了元大都遗址公园的白海棠,又特地绕远坐地铁看了两次大钟寺站旁边开得密不成样的桃花。书就一直搁着。拜大风天所赐,终于看完了延宕好久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我本来记性就不好,勒卡雷的小说又人物众多,时间拖得一长,就老是忘了前情。难怪他的书都要有人物表,我特地折起那一页,新出场一个人就翻回去看,到底谁是“剥头皮组”的,谁是“点路灯组”的。中间有点不耐烦,几乎迷失了,结果一到结尾,并不是恍然大悟,反而是一种反高潮的黯然神伤。我也挺莫名其妙:他并没抛出什么重量级的煽情手榴弹,怎么我就感伤了。大概是开头和结尾密密衔接了起来,那种最普通的小男孩的眼睛所看到普通的一幕,衬托着那个既不是主角也不是英雄的前特工惊人的过去,而他也不过是为了衬托史迈利挖出来的内鬼,那君子人儿的悲剧性。
还有安,史迈利的太太,也是他永远得不到的女人,像个鬼魂儿一样氤氲在他孤零零的生活里。加重了这种愁苦的气氛。
真见鬼,我本来读的是所谓的硬汉小说,一个是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一个是《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没想到一个比一个弯,一个比一个酸的馒头(sentimental)!看得我又爱又恨。
12:26:57 -
barb -
23 April
天色
以前看师太小说,印象最深的倒不是所谓名言警句,而是她笔下千变万化的天色,蛋壳青、淡紫、灰蓝……还有像怪兽一样吞吃天空的乌云,火一样的影树。小说早烦了,这个百看不厌。
今在杂志看到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独脚将军陈策带着一批英国军人突围泅水到惠州的故事。这些军人无论中英,竟都有日记留下来。其中一个叫McEwan的英国军官在当年圣诞节,即突围当天记下的日记有这么一段:
“日色将暮,仍无信号。七点。七点半。八点,终于有了。感觉上我们经过了非常漫长的等待。船驶了出来,我看见我在香港见过的最美丽的傍晚。南丫岛之西,残余的淡紫色的晚霞,钢灰色的天空有星光零散闪耀,右舷之大屿山在兀自一大片深紫之中呈现错落的灯火。在我们背后薄扶林一座建筑物疯也似的发亮,乌黑的浓烟冉冉升到夜空,远方火焰可见。船上凝聚着一种说不出的悲剧感:香港沦陷了。仅仅十七日。现在我们正朝向中国进发……”
一下就想起师太小说。原来那不仅仅是描写,是人所共见的维港美景。
今在杂志看到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独脚将军陈策带着一批英国军人突围泅水到惠州的故事。这些军人无论中英,竟都有日记留下来。其中一个叫McEwan的英国军官在当年圣诞节,即突围当天记下的日记有这么一段:
“日色将暮,仍无信号。七点。七点半。八点,终于有了。感觉上我们经过了非常漫长的等待。船驶了出来,我看见我在香港见过的最美丽的傍晚。南丫岛之西,残余的淡紫色的晚霞,钢灰色的天空有星光零散闪耀,右舷之大屿山在兀自一大片深紫之中呈现错落的灯火。在我们背后薄扶林一座建筑物疯也似的发亮,乌黑的浓烟冉冉升到夜空,远方火焰可见。船上凝聚着一种说不出的悲剧感:香港沦陷了。仅仅十七日。现在我们正朝向中国进发……”
一下就想起师太小说。原来那不仅仅是描写,是人所共见的维港美景。
20:14:50 -
barb -
20 April
漫漫
十七日,急冻奇侠三人组总算沾染到夏天的热乎劲儿,化身榴莲飘飘三人组(大嚼榴莲糖,真是臭味相投),进行某人开拔前最后一次活动,看北京现代舞展演周第三天的演出(共五天)。
从台上,到台下,这是一次散漫的演出,简直散发着风柜来的人那样无所事事的气场,连座位都不对号。排队时我四面八方一看,人头涌涌,都是年轻的脑袋。还没感慨完,我的著名容易被陌生人打招呼脸就发挥了作用,一大妈在加塞请求得到许可后竟然跟我聊起了摩登舞,还热情地忽悠大家去跳——她的目光扫视一圈,准确地落在身光颈靓的某人身上,大胆挑逗道:我看你挺时尚的嘛,你就可以跳……
于是一开场,就和上了第一支舞《玄梦三折》婚恋嫁娶的伧俗热闹。剧场小,我们又一早占住第三排座位,虽然不至于和舞者呼吸相闻,看就完全不费力气。我唯一动用望远镜的时刻是一个舞者蹲下来背对观众——竟然露出内裤,我实在按捺不住望了一下,原来是老好CK,一点惊喜没有:evil:
我比较喜欢黑衣群舞里头的矮个儿秃头dd,跳“男生女相”很有一腿,我很喜欢这样的疯魔,几乎怀疑他是编舞黄磊来着。后来在派发的书签里看到黄的照片才发现不是的,不过黄编舞真是个文艺青年,舞码都叫《风生水起》、《此去经年》这样文绉绉的名字。
第二段舞《秉持着悲观与绝望》是自编自舞,跳舞的mm明显不够芭蕾舞娘下半身比上半身长11.5厘米的苛求,可是像邓肯说的芭蕾和一切人类情感背道而驰,现代舞者们大概心想,管他的芭蕾呐,就不管不顾地跳将起来。她跳得真挚,下半截我几乎感动了起来,并不为了舞姿,而是为了可以这样大喊着绝望的肆无忌惮的青春。小mm生着一张白腻的脸,清秀而坚毅,有一点点肉感,像某个韩国演员,也许是郑由美。
第三支是雷动天下的舞《寻找我的阳光旅程之一》——曹诚渊为了舞蹈周blog都不写了,估计台下紧盯着这一支。舞当然是好的,凭呼吸的韵律,奏鸾凤之和鸣……哎我又想歪了,其实人家是很健康的一支舞,还挺和谐的。许一鸣跳舞的功夫显然不如编舞,和舞伴差了那么一丁点儿默契。之二之三不知是什么,如果都是这么明朗的,可以叫“背弃了悲观与绝望”,现身说法中年版。
第四支《零点零分的寂静》,hans说像办公室纠葛,全中。
第五支《梦想街道》……简直从名字起就很春晚,含有春晚所需要的一切元素,尤其是突兀的煽情。这种以青春为名的激情,你真说不好该鼓励还是该打击,多少有些尴尬。
第六支我完全没印象了,可见不是佳作。
第七支《因为我爱它》乃当晚最神奇爆笑舞码,hans一直在我旁边颤抖,时不时绷不住笑出声来,我怀疑都给台上的英国mm看到了,不过不要紧,反正她跳的是瑜伽……该情该景,只有《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里黄韵诗的闻铃一舞可与之媲美。
第八支,乃一支不可言说之舞,其奇情其香艳其摧枯拉朽……还是留给high翻的某人说罢。既然fuge把节目单谦让给我,姑且照抄一下宣传语:“在军营中,智慧灵性的动物——军犬,被战士称为‘无言的战友’(即舞码的名字)。本舞蹈通过描述战士与狗一起玩耍、共同战斗的情节,表达出了战士与狗之间兄弟般的情谊和难以分割的感情。”——好事者请往十万八千里外想象(神奇的是编舞有战友文工团公职及若干正经舞蹈协会副职)。这是当晚一大惊喜,况且一人一狗都是帅哥:mrgreen:
第九支《独舞》是我最讨厌的超级自恋之舞,应该请小船在越南的心理医生诊治一下。
最后一支,fuge说可以叫“黄色娘子军”,舞者有二十来个,舞服黄澄澄一片,音乐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舞蹈学院的,算专业水平,场子走得圆圆的,倒像是京戏,杀气腾腾、昂扬地。恰到好处的压轴戏。
十支舞从头到尾,排得真是煞费苦心。再业余水平,能凑出五天的舞,还并不算太欺场,已经十分难得。我后悔没早买十九日的票——有邢亮独舞《一切随风而逝》,票一周前就卖光了,看来比我们在乎的人很多。
仓促相遇的舞者,转瞬不知有没有再见的机会呢。匆匆两小时,不像看表演,倒像是彩排,有种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的亲近的距离感。现场常有录像三倍的魅力,与顶尖舞团的差距(大概十倍不止)于此多少补上了。像乡下看戏,一出花脸,一套河北梆子,露天的夜里,草草地看了,只觉得好,因咂摸的是瞬间此时,片刻前响当当的存在轰地没了,空气里倒像尚有余音。这兴奋要走过打烊的东方广场,到地铁站里才慢慢褪掉。
舞蹈之路何其漫漫,但愿多给他们一点这样蚁民的掌声。
从台上,到台下,这是一次散漫的演出,简直散发着风柜来的人那样无所事事的气场,连座位都不对号。排队时我四面八方一看,人头涌涌,都是年轻的脑袋。还没感慨完,我的著名容易被陌生人打招呼脸就发挥了作用,一大妈在加塞请求得到许可后竟然跟我聊起了摩登舞,还热情地忽悠大家去跳——她的目光扫视一圈,准确地落在身光颈靓的某人身上,大胆挑逗道:我看你挺时尚的嘛,你就可以跳……
于是一开场,就和上了第一支舞《玄梦三折》婚恋嫁娶的伧俗热闹。剧场小,我们又一早占住第三排座位,虽然不至于和舞者呼吸相闻,看就完全不费力气。我唯一动用望远镜的时刻是一个舞者蹲下来背对观众——竟然露出内裤,我实在按捺不住望了一下,原来是老好CK,一点惊喜没有:evil:
我比较喜欢黑衣群舞里头的矮个儿秃头dd,跳“男生女相”很有一腿,我很喜欢这样的疯魔,几乎怀疑他是编舞黄磊来着。后来在派发的书签里看到黄的照片才发现不是的,不过黄编舞真是个文艺青年,舞码都叫《风生水起》、《此去经年》这样文绉绉的名字。
第二段舞《秉持着悲观与绝望》是自编自舞,跳舞的mm明显不够芭蕾舞娘下半身比上半身长11.5厘米的苛求,可是像邓肯说的芭蕾和一切人类情感背道而驰,现代舞者们大概心想,管他的芭蕾呐,就不管不顾地跳将起来。她跳得真挚,下半截我几乎感动了起来,并不为了舞姿,而是为了可以这样大喊着绝望的肆无忌惮的青春。小mm生着一张白腻的脸,清秀而坚毅,有一点点肉感,像某个韩国演员,也许是郑由美。
第三支是雷动天下的舞《寻找我的阳光旅程之一》——曹诚渊为了舞蹈周blog都不写了,估计台下紧盯着这一支。舞当然是好的,凭呼吸的韵律,奏鸾凤之和鸣……哎我又想歪了,其实人家是很健康的一支舞,还挺和谐的。许一鸣跳舞的功夫显然不如编舞,和舞伴差了那么一丁点儿默契。之二之三不知是什么,如果都是这么明朗的,可以叫“背弃了悲观与绝望”,现身说法中年版。
第四支《零点零分的寂静》,hans说像办公室纠葛,全中。
第五支《梦想街道》……简直从名字起就很春晚,含有春晚所需要的一切元素,尤其是突兀的煽情。这种以青春为名的激情,你真说不好该鼓励还是该打击,多少有些尴尬。
第六支我完全没印象了,可见不是佳作。
第七支《因为我爱它》乃当晚最神奇爆笑舞码,hans一直在我旁边颤抖,时不时绷不住笑出声来,我怀疑都给台上的英国mm看到了,不过不要紧,反正她跳的是瑜伽……该情该景,只有《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里黄韵诗的闻铃一舞可与之媲美。
第八支,乃一支不可言说之舞,其奇情其香艳其摧枯拉朽……还是留给high翻的某人说罢。既然fuge把节目单谦让给我,姑且照抄一下宣传语:“在军营中,智慧灵性的动物——军犬,被战士称为‘无言的战友’(即舞码的名字)。本舞蹈通过描述战士与狗一起玩耍、共同战斗的情节,表达出了战士与狗之间兄弟般的情谊和难以分割的感情。”——好事者请往十万八千里外想象(神奇的是编舞有战友文工团公职及若干正经舞蹈协会副职)。这是当晚一大惊喜,况且一人一狗都是帅哥:mrgreen:
第九支《独舞》是我最讨厌的超级自恋之舞,应该请小船在越南的心理医生诊治一下。
最后一支,fuge说可以叫“黄色娘子军”,舞者有二十来个,舞服黄澄澄一片,音乐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舞蹈学院的,算专业水平,场子走得圆圆的,倒像是京戏,杀气腾腾、昂扬地。恰到好处的压轴戏。
十支舞从头到尾,排得真是煞费苦心。再业余水平,能凑出五天的舞,还并不算太欺场,已经十分难得。我后悔没早买十九日的票——有邢亮独舞《一切随风而逝》,票一周前就卖光了,看来比我们在乎的人很多。
仓促相遇的舞者,转瞬不知有没有再见的机会呢。匆匆两小时,不像看表演,倒像是彩排,有种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的亲近的距离感。现场常有录像三倍的魅力,与顶尖舞团的差距(大概十倍不止)于此多少补上了。像乡下看戏,一出花脸,一套河北梆子,露天的夜里,草草地看了,只觉得好,因咂摸的是瞬间此时,片刻前响当当的存在轰地没了,空气里倒像尚有余音。这兴奋要走过打烊的东方广场,到地铁站里才慢慢褪掉。
舞蹈之路何其漫漫,但愿多给他们一点这样蚁民的掌声。
22:20:40 -
barb -
18 April
家常
到燕郊探妈妈,路上见到意外的风光:数以亩计的桃花,浓粉淡粉翠绿。没绿起来的草坡开满紫花,和枯草掺和着,像一片片云。白丁香、杏花都开了。坡地上几群羊啃着嫩芽,池塘水光相映。不能相信这是离北京咫尺之地,若不是后面的高楼煞风景,倒和Olimpia(我妹)写的Leeds春日有几分相像。可惜坐在公交车上,不能跳下高速公路去玩耍。
连Cathayan三人午饭后上超市,买了新上市的香椿芽、蚕豆、水萝卜、猪肘子一大只,和我最喜欢的哈尔滨啤酒。回来和妈妈看新得的《兰庭六记》百变昆生折子戏,听昆曲还是人多好,评头论足,一个人看寂寞。然后就是必然的草堂春睡,窗外日迟。每到妈妈这里,总觉落入时间的荒野,身外事摈于门外,特别放心、安定,因此睡得沉。
结果半路被老爸电话吵醒,听说我在妈妈处,立刻吞吞吐吐不知所云。我正怀疑他是不是闹更年期,突然门铃响,他就进来了,施施然拎着四支雪糕,我们都惊了。话说我们一家四口生活在四个地方,简直动如参与商,像这样未经约定凑足三口的会面实属意外之喜。
喝着啤酒吃饭聊天时才知,他昨晚住在金宝街的鄂尔多斯艾力(艾力是蒙古话村子的意思)酒店,而我在数百米外的东方先锋剧场看现代舞。
神叨叨晚饭对话一段:
我(讨好地):我特理解我爸,因为我们都是AB型!(面向A型的老妈)
我爸(吃惊):你也是AB型?
我(更吃惊):对啊!Olimpia也是AB型!
我爸(大惊):不是吧???!
连Cathayan三人午饭后上超市,买了新上市的香椿芽、蚕豆、水萝卜、猪肘子一大只,和我最喜欢的哈尔滨啤酒。回来和妈妈看新得的《兰庭六记》百变昆生折子戏,听昆曲还是人多好,评头论足,一个人看寂寞。然后就是必然的草堂春睡,窗外日迟。每到妈妈这里,总觉落入时间的荒野,身外事摈于门外,特别放心、安定,因此睡得沉。
结果半路被老爸电话吵醒,听说我在妈妈处,立刻吞吞吐吐不知所云。我正怀疑他是不是闹更年期,突然门铃响,他就进来了,施施然拎着四支雪糕,我们都惊了。话说我们一家四口生活在四个地方,简直动如参与商,像这样未经约定凑足三口的会面实属意外之喜。
喝着啤酒吃饭聊天时才知,他昨晚住在金宝街的鄂尔多斯艾力(艾力是蒙古话村子的意思)酒店,而我在数百米外的东方先锋剧场看现代舞。
神叨叨晚饭对话一段:
我(讨好地):我特理解我爸,因为我们都是AB型!(面向A型的老妈)
我爸(吃惊):你也是AB型?
我(更吃惊):对啊!Olimpia也是AB型!
我爸(大惊):不是吧???!
19:51:31 -
barb -
15 April
怪癖
昨下班买了三朵拳头大白玫瑰。刚插进瓶子,白毛小子就冲上来——好久没尝鲜了,大口咬叶子,险些把花瓶扯翻。他爱吃的叶子计有百合、玫瑰、康乃馨……风信子是不吃的,据说对猫有毒。Cathayan曾经种过麦子给他吃,次次津津有味。咪咪也没什么别的爱好,就是睡和吃。饭盆一空就恐慌,大概是流浪时的心理阴影。不挑食,吃饱就睡。睡的时候脸冲下,右爪捂着脑袋,Cathayan说他睡得越来越像人。
波波富贵惯了,对吃没什么兴趣,怪看不惯这种没气质的行为,甚至挑剔到不爱和咪咪一个盆里喝水。他的怪癖是每天要喝新鲜的水。一听到我们睡醒的动静,就嗷嗷地在门外叫,直到你把自来水龙头打开。水不能大,要一滴滴地漏,他伸舌头吧嗒吧嗒舔,水积多了浸湿爪子也不管(平时最讨厌水),别提多香甜了。咪咪对这种小资行径大概也是很不屑的,自顾自走开,盼望着天上掉妙鲜包。没有妙鲜包,玉米也是可以吃一吃的。

波波富贵惯了,对吃没什么兴趣,怪看不惯这种没气质的行为,甚至挑剔到不爱和咪咪一个盆里喝水。他的怪癖是每天要喝新鲜的水。一听到我们睡醒的动静,就嗷嗷地在门外叫,直到你把自来水龙头打开。水不能大,要一滴滴地漏,他伸舌头吧嗒吧嗒舔,水积多了浸湿爪子也不管(平时最讨厌水),别提多香甜了。咪咪对这种小资行径大概也是很不屑的,自顾自走开,盼望着天上掉妙鲜包。没有妙鲜包,玉米也是可以吃一吃的。

20:28:51 -
barb -
14 April
糖果
春天来了,出门的人多起来。于是桌子上常常出现一些吃的东西。最喜欢的是谁从泰国带回来的一种榴莲拖肥,用彩色蜡纸包着,桔红、绿、黄,裹得简单草率,一拉就露出啡色圆墩墩的糖,总之有种手到擒来的诱惑。我起先怀疑它是臭的——我吃不了榴莲,除了榴莲酥。冒险试了一下,不臭,越吃越香甜。吃了一只,又一只,又一只,又一只……它的味道和四洲之类的零食店的榴莲糖不一样,特别黏牙,特别糯,还有点椰子香,又不过分甜,谁知道哪儿有卖的,一定告诉我。
同事老好Yi桑被派到东京工作,次次回来带些小零食给我,和以前btsb在晚插秧大学读书时带给我们的和果子差不多。Yi桑自己的口味奇突,对那些我一吃就吐掉的瑞典咸味甘草糖(我觉得是八角味)甘之如饴。我正在纳闷她的口味怎么大众化起来,她就给我一种昆布果子吃。样子是黑乎乎口香糖大小的一条一条,很薄,怀疑是海带,至少也是海藻的一种。上面沾着一层白色粉末。白粉是酸的,昆布是咸的,有点像话梅,偏又软软烂烂,似乎有点发酵……总之五味杂陈。她老板T先生说,这是很古老的一种日本传统食品,他忙不迭地拿去和别的日本同事分享了。这个东西,在我的心里可以和瑞典甘草糖媲美,但是据说非常健康。

同事老好Yi桑被派到东京工作,次次回来带些小零食给我,和以前btsb在晚插秧大学读书时带给我们的和果子差不多。Yi桑自己的口味奇突,对那些我一吃就吐掉的瑞典咸味甘草糖(我觉得是八角味)甘之如饴。我正在纳闷她的口味怎么大众化起来,她就给我一种昆布果子吃。样子是黑乎乎口香糖大小的一条一条,很薄,怀疑是海带,至少也是海藻的一种。上面沾着一层白色粉末。白粉是酸的,昆布是咸的,有点像话梅,偏又软软烂烂,似乎有点发酵……总之五味杂陈。她老板T先生说,这是很古老的一种日本传统食品,他忙不迭地拿去和别的日本同事分享了。这个东西,在我的心里可以和瑞典甘草糖媲美,但是据说非常健康。

21:02:58 -
barb -
12 April
返乡
随Cathayan回乡下参加上上辈的葬礼。回来后换衣服,抖落一地土。向妈妈汇报,老妈说没有土,哪有人。膝盖也疼,磕了不知多少个头。同是北方农村,河南的讲究和河北截然不同。河北铺张,规矩上却不如中原多。这两日我常常走错地方,执错东西,因是外省媳妇,人家只会说一句“我们这里不是这样的规矩”,而不会怪罪有失礼数。
我从没在这个季节去过乡下,以外地人眼光看,只觉得什么都好。麦田油绿,我刚开始还以为是葱。桐树开着粉紫色的花, Cathayan说今年雨水不好,没有开成他小时候那样满村都是,一蓬一蓬的。油菜花黄黄的开得正旺,还真有扎着稻草人的。最好看的是苹果花,一片片绿林子夹着白花,太远闻不见味,却老觉得是清甜的。
下葬时天暴热。按当地规矩,人手一枝柳条做的“哭丧棒”要插到坟头上,如果雨水好,有的柳枝会发芽长成小树。这时候可以脱下孝服了:女子是斜襟,男子是对襟。媳妇的头巾要在尾端结个布疙瘩,拿麻绳扎在腰里。女儿的则扎成花。
从地里往家里走,我们忙着东张西望,远远地落在后头。忽然二弟三弟在远处喊起来,跑过去一看,一只头顶有冠尾巴有黑白纹的鸟怪神气地在地上溜达。二弟替我拍照,一惊,鸟飞起来,冠子张得大大的,漂亮极了。我才知道这就是啄木鸟!Cathayan不能相信我竟然从没见过。他说这鸟是公的。
三弟不知从哪儿折了枝花给我,小白花,紫芯,一串串垂挂着,闻着很香。拿回家,借花献佛,送给二弟的女儿妞妞。妞妞说,谢谢娘——娘——。她向Cathayan叫大伯,按此地叫法,我自然成了大娘,口头就叫“娘”。四岁半的妞妞偷偷地跟弟妹说怎么也叫不出口,因为觉得这个叫法好老。
下午搭表弟的车回郑州。因为多年前第一次去婆家就把一大碗烩面吃了个底儿朝天,从此成了笑柄,表弟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大嫂,吃烩面去?总之不由分说地把我们拉去了火车站旁边的萧记,给我点了个大碗。第一次吃烩面的时候,表弟和三弟都是小男生,大学还没毕业,现在却都到了必须考虑婚姻大事的年纪。表弟以前瘦高,虽然从来不是帅哥,穿制服还是英挺的,现在胖了很多,简直像个中年汉子。三弟的腰围则不让他大哥。在我们自己身上还没觉得日子过得快,看见他们才惊觉,时间都到哪去了。
我从没在这个季节去过乡下,以外地人眼光看,只觉得什么都好。麦田油绿,我刚开始还以为是葱。桐树开着粉紫色的花, Cathayan说今年雨水不好,没有开成他小时候那样满村都是,一蓬一蓬的。油菜花黄黄的开得正旺,还真有扎着稻草人的。最好看的是苹果花,一片片绿林子夹着白花,太远闻不见味,却老觉得是清甜的。
下葬时天暴热。按当地规矩,人手一枝柳条做的“哭丧棒”要插到坟头上,如果雨水好,有的柳枝会发芽长成小树。这时候可以脱下孝服了:女子是斜襟,男子是对襟。媳妇的头巾要在尾端结个布疙瘩,拿麻绳扎在腰里。女儿的则扎成花。
从地里往家里走,我们忙着东张西望,远远地落在后头。忽然二弟三弟在远处喊起来,跑过去一看,一只头顶有冠尾巴有黑白纹的鸟怪神气地在地上溜达。二弟替我拍照,一惊,鸟飞起来,冠子张得大大的,漂亮极了。我才知道这就是啄木鸟!Cathayan不能相信我竟然从没见过。他说这鸟是公的。
三弟不知从哪儿折了枝花给我,小白花,紫芯,一串串垂挂着,闻着很香。拿回家,借花献佛,送给二弟的女儿妞妞。妞妞说,谢谢娘——娘——。她向Cathayan叫大伯,按此地叫法,我自然成了大娘,口头就叫“娘”。四岁半的妞妞偷偷地跟弟妹说怎么也叫不出口,因为觉得这个叫法好老。
下午搭表弟的车回郑州。因为多年前第一次去婆家就把一大碗烩面吃了个底儿朝天,从此成了笑柄,表弟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大嫂,吃烩面去?总之不由分说地把我们拉去了火车站旁边的萧记,给我点了个大碗。第一次吃烩面的时候,表弟和三弟都是小男生,大学还没毕业,现在却都到了必须考虑婚姻大事的年纪。表弟以前瘦高,虽然从来不是帅哥,穿制服还是英挺的,现在胖了很多,简直像个中年汉子。三弟的腰围则不让他大哥。在我们自己身上还没觉得日子过得快,看见他们才惊觉,时间都到哪去了。
13:55:05 -
barb -
07 April
一点一点
去影院看《东邪西毒》终极版,连我俩统共没几个人,快结尾时还有人大声打电话,可知是临时凑热闹的,早被电影烦死了。
说它不好的人太多,我看了倒觉得不错,原本没有把它放在那样高的地位。
难怪放在四月上映,这一版是彻头彻尾的张国荣的电影,光看他的脸好了,千变万化。那种讥诮的表情,以前从来没在他脸上出现过。怪就怪在他圈在那种沙窝里竟不烦,无论怎么精致,男人总是比女人好熬苦。
说到底,仍然是个明信片电影,虽然总算把故事讲囫囵了。
大概是九五年,不记得为什么有碟没有影碟机,由好友Z带我去他老师家看,还有老师上高中的儿子,四个人默不作声地看了《东邪西毒》和《好人寥寥》(A Few Good Men)。记得看到女人的手在男人身上游走时,感觉很尴尬,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观众组合。事后Z听说他们非常不喜欢,我才隐约想到人和人根深蒂固的差异。我当时很喜欢王家卫,现在想起来,不是为了电影,而是明信片。一祯一祯,支离破碎。我欣赏的是静止,不是流动。内心独白是明信片背面的字,有一搭没一搭,寄自天涯海角,总之我能想到最远的地方。
魏绍恩在《四出王家卫,洛杉矶。》里写过:“对于这高佬,《东邪西毒》更大的意义,在他把整个人投了进去,他的所思所想他看待电影的态度他看待生命的态度他的坚持执著他的不离不弃,他把1992年至1994年的王家卫全数放进去,因为他知道,过了这阶段,他就会变,变得更成熟变得更世故变得更通情达理变得更老,而他同时知道,随着这些变,他会一点一点忘记,他会一点一点变得开始不再认识这阶段的自己。在这名高佬开始忘记以前,他乐意把一切投到这部电影里面,放进时间的锦囊。”
终极版就是一个更世故更通情达理的版本,所谓年少时清明的理想渐渐远去。这种圆熟亦好。模糊的画面,一本正经赶不上趟的配音,就都觉得无所谓。看着银幕上一张张巨大的脸,只觉得津津有味:张曼玉的脸真是美,梁家辉放在这一群人里真不搭(张学友都好搭,旺角卡门起就搭。梁家辉的位置是《天台的月光》),杀马贼的动作好像现代舞……
当年还没迷上张叔平,一心喜欢剪接谭家明,一个活的,叫家明的男人!:mrgreen:
后来发现他做导演很不靠谱,石琪评他很有一套,想起他的浪漫开篇总以乱砍乱杀结尾,我就想笑。
终极版是他和张叔平一起剪的,可见连导演三个人都老了,懒得作新锐状。其实我最爱他的剪接是《天长地久》,刘德华砸照相馆玻璃(偷刘锦玲照片)那幕前后出现两次,第一次令人费解,第二次教人唏嘘。
于是我就突然怀念起那些动人的老香港电影了。
说它不好的人太多,我看了倒觉得不错,原本没有把它放在那样高的地位。
难怪放在四月上映,这一版是彻头彻尾的张国荣的电影,光看他的脸好了,千变万化。那种讥诮的表情,以前从来没在他脸上出现过。怪就怪在他圈在那种沙窝里竟不烦,无论怎么精致,男人总是比女人好熬苦。
说到底,仍然是个明信片电影,虽然总算把故事讲囫囵了。
大概是九五年,不记得为什么有碟没有影碟机,由好友Z带我去他老师家看,还有老师上高中的儿子,四个人默不作声地看了《东邪西毒》和《好人寥寥》(A Few Good Men)。记得看到女人的手在男人身上游走时,感觉很尴尬,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观众组合。事后Z听说他们非常不喜欢,我才隐约想到人和人根深蒂固的差异。我当时很喜欢王家卫,现在想起来,不是为了电影,而是明信片。一祯一祯,支离破碎。我欣赏的是静止,不是流动。内心独白是明信片背面的字,有一搭没一搭,寄自天涯海角,总之我能想到最远的地方。
魏绍恩在《四出王家卫,洛杉矶。》里写过:“对于这高佬,《东邪西毒》更大的意义,在他把整个人投了进去,他的所思所想他看待电影的态度他看待生命的态度他的坚持执著他的不离不弃,他把1992年至1994年的王家卫全数放进去,因为他知道,过了这阶段,他就会变,变得更成熟变得更世故变得更通情达理变得更老,而他同时知道,随着这些变,他会一点一点忘记,他会一点一点变得开始不再认识这阶段的自己。在这名高佬开始忘记以前,他乐意把一切投到这部电影里面,放进时间的锦囊。”
终极版就是一个更世故更通情达理的版本,所谓年少时清明的理想渐渐远去。这种圆熟亦好。模糊的画面,一本正经赶不上趟的配音,就都觉得无所谓。看着银幕上一张张巨大的脸,只觉得津津有味:张曼玉的脸真是美,梁家辉放在这一群人里真不搭(张学友都好搭,旺角卡门起就搭。梁家辉的位置是《天台的月光》),杀马贼的动作好像现代舞……
当年还没迷上张叔平,一心喜欢剪接谭家明,一个活的,叫家明的男人!:mrgreen:
后来发现他做导演很不靠谱,石琪评他很有一套,想起他的浪漫开篇总以乱砍乱杀结尾,我就想笑。
终极版是他和张叔平一起剪的,可见连导演三个人都老了,懒得作新锐状。其实我最爱他的剪接是《天长地久》,刘德华砸照相馆玻璃(偷刘锦玲照片)那幕前后出现两次,第一次令人费解,第二次教人唏嘘。
于是我就突然怀念起那些动人的老香港电影了。
22:16:44 -
barb -
06 April
红玫瑰
去梅剧院看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和才子阿库汉(Akram Khan)的“我之深处”(In-I)——不枉小山为它盖棺定论,像话剧多过现代舞。那大段大段的念白,较让人诧异于阿库汉的“演技”,本来揣测舞者更善于用肢体表白的嘛,他却说得有声有色,一个人可成一台戏。换过来,对影后因为期望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近似凄厉的大声独白多少觉得虚假,回荡到我们高高在上的四层楼座,我有点bored。因此一直执念于技术问题:她是怎么被挂到红色背景墙上的?虽然邻居给我讲解,必然有个钩子在后面钩着,我一直杞人忧天地替她累,又怕她掉下来。
这是头一次参加这么浩浩荡荡(以赋格为核心)的观舞团,很有流落江湖的小弟终于找到黑社会组织的扬眉吐气感。
还是大佬有水平,一句刻薄话说到我心上去:比诺什和阿库汉的双人舞,像公园里徒弟跟着师父打太极,是跟着,不是竞技。
我一向不喜欢比佳人,但颇佩服她四十多改跳舞的勇气,只是看她跳舞的确较像我们去娱乐她,而不是她娱乐我们……
汉才子呢,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迁就半路出家的女士,动作集中在手上(赋格说有孟加拉印度系的关系,有道理),虽然也好看,始终现代舞的根基在腿上。但是那是和天后(Sylvie Guillem)共舞过的编舞!在这个现代舞的边缘地能看到这些传奇的身边人已经够好了。
搞笑的是我们高高在上的四层看不到舞台深处和两侧——因为京剧舞台断不会跑到那里勾当,偏偏男女主角总在关键时刻跑到墙角去,要么看不到,要么只有下半身,说多暧昧有多暧昧,急得我们抓耳挠腮。身边的帅哥一直撅着屁股探出头去,以猴子捞月的姿势企图看多一眼,再多一眼。我们坐东厢,散场和西厢三位一碰面,都说今儿看的是删节版……
那边厢Nashy也从《玉簪记》归来,啊我的白玫瑰!
这是头一次参加这么浩浩荡荡(以赋格为核心)的观舞团,很有流落江湖的小弟终于找到黑社会组织的扬眉吐气感。
还是大佬有水平,一句刻薄话说到我心上去:比诺什和阿库汉的双人舞,像公园里徒弟跟着师父打太极,是跟着,不是竞技。
我一向不喜欢比佳人,但颇佩服她四十多改跳舞的勇气,只是看她跳舞的确较像我们去娱乐她,而不是她娱乐我们……
汉才子呢,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迁就半路出家的女士,动作集中在手上(赋格说有孟加拉印度系的关系,有道理),虽然也好看,始终现代舞的根基在腿上。但是那是和天后(Sylvie Guillem)共舞过的编舞!在这个现代舞的边缘地能看到这些传奇的身边人已经够好了。
搞笑的是我们高高在上的四层看不到舞台深处和两侧——因为京剧舞台断不会跑到那里勾当,偏偏男女主角总在关键时刻跑到墙角去,要么看不到,要么只有下半身,说多暧昧有多暧昧,急得我们抓耳挠腮。身边的帅哥一直撅着屁股探出头去,以猴子捞月的姿势企图看多一眼,再多一眼。我们坐东厢,散场和西厢三位一碰面,都说今儿看的是删节版……
那边厢Nashy也从《玉簪记》归来,啊我的白玫瑰!
08:07:56 -
barb -
05 April
时髦
召集腐败的时候,不爱正在香港出差,电话那头兴冲冲地讲,哎你知道吗,我买到了《小团圆》!被我一盆冷水泼过去,老大,现在人手一本《小团圆》好不好。
欣叶腐败现场,姗姗来迟的习习也噌地掏出一本《小团圆》印证啥是当今时髦女郎随身装备。
但大姐头锲而不舍地又买了《对照记》,虽然她信誓旦旦以后都改看繁体竖排版,《对照记》倒不是的。当我一盆“早出过简体版了又平又靓”的冷水又待泼过去,才发现,的确内容还是不一样。她在出差的间隙两天就把《小团圆》读完,跟我们讲,看过《对照记》,板上钉钉,都是真的。
奇就奇在话题都集中在二婶身上,从她的美貌(有照片为证)、摩登、矛盾、新女性的挣扎、当妈的本分……一路说下去,不知道初为人母的小涵是不是被不体贴的我们多加一重心理负担。
王德威的《落地的麦子不死》写“张派传人”,有朱氏姐妹、施叔青、苏伟贞、钟晓阳、黄碧云、王安忆、须兰、袁琼琼……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倪师太,大概不够上纯文学的台面。但当然她是张派传人。而二婶和九莉的纠结,最适合用她的名言改编:都是时代的错。如果二婶得到过现代育儿教育的哪怕一点点启发,大抵不会这样。当然没有这么多的痛苦,也没有这样的小说。照概率看,天才不该是不世出的,只是或许,有些被幸福生活埋没了。
花团锦簇的《小团圆》的评论里,我其实最想看王德威,似乎他还没写?
在我的忽悠下,不爱和Ithaca又人手一本四月明日风尚,为了附赠的张爱玲detached别册——我虽然不是张迷,对她的手稿、美国身份证……这些杂七杂八“活过”的证据还是爱看的。虽然马家辉再次大洒狗血,总算是惠民一次。然后,细心的I小姐指出,设计是陆智昌。难怪素净的风格似曾相识。
欣叶腐败现场,姗姗来迟的习习也噌地掏出一本《小团圆》印证啥是当今时髦女郎随身装备。
但大姐头锲而不舍地又买了《对照记》,虽然她信誓旦旦以后都改看繁体竖排版,《对照记》倒不是的。当我一盆“早出过简体版了又平又靓”的冷水又待泼过去,才发现,的确内容还是不一样。她在出差的间隙两天就把《小团圆》读完,跟我们讲,看过《对照记》,板上钉钉,都是真的。
奇就奇在话题都集中在二婶身上,从她的美貌(有照片为证)、摩登、矛盾、新女性的挣扎、当妈的本分……一路说下去,不知道初为人母的小涵是不是被不体贴的我们多加一重心理负担。
王德威的《落地的麦子不死》写“张派传人”,有朱氏姐妹、施叔青、苏伟贞、钟晓阳、黄碧云、王安忆、须兰、袁琼琼……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倪师太,大概不够上纯文学的台面。但当然她是张派传人。而二婶和九莉的纠结,最适合用她的名言改编:都是时代的错。如果二婶得到过现代育儿教育的哪怕一点点启发,大抵不会这样。当然没有这么多的痛苦,也没有这样的小说。照概率看,天才不该是不世出的,只是或许,有些被幸福生活埋没了。
花团锦簇的《小团圆》的评论里,我其实最想看王德威,似乎他还没写?
在我的忽悠下,不爱和Ithaca又人手一本四月明日风尚,为了附赠的张爱玲detached别册——我虽然不是张迷,对她的手稿、美国身份证……这些杂七杂八“活过”的证据还是爱看的。虽然马家辉再次大洒狗血,总算是惠民一次。然后,细心的I小姐指出,设计是陆智昌。难怪素净的风格似曾相识。
08:15:55 -
barb -
04 April
毒笑话
昨Anna出差最后一天,同我们一起参加欢迎新同事的午餐聚会,J同事开车,拉着她、我和美女同事。回来时,Anna突然在马路上看到一头驴,友邦惊诧道,北京难道常常能在马路上看到驴吗。我说不会啊,她说啊哈,希望那不是咱们公司里的经理……
08:18:45 -
barb -
03 April
反战
跟瑞典男人婆恶斗两天,终于取得阶段性胜利。头一天Anna没倒过来时差,搞不清状况,敌我不分,变成两条强龙斗我这条地头蛇。两个人跟捧哏逗哏一样你说上句我说下句滔滔不绝,英文简直说得比瑞典话还好,我只能夹缝里求生存。第二天我改变战略摇身一变恶婆娘,叉着腰不许她们开口非得让我说完,在我声情并茂七情上面的慷慨陈词下,Anna幡然醒悟我们是一个壕里的战友,开始提供掩护,终于恢复了双煞大战男人婆的威水状态,走向了所谓的双赢(为免两败俱伤的妥协)。掐指一算,我退了一小步,换她退两大步,划算。
黄昏时分,本地业务大佬特地走到老板和我座位前,说男人婆赞叹,巴巴拉很棒,虽然很tough。我生气地想,你才tough呢,你们全家都tough。
我怎么被血淋淋的工作逼成了这么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挑衅者。想当初面试的时候老被猎头质问,哎,你这么不aggressive怎么能有竞争性呀,跟了老板又说,哎你这么不proactive需要加把劲了。千锤百炼得我变成这样一个咄咄逼人的怪兽。
美女同事在班车教育我一路,说我工作状态过于紧张,弦绷得嗡嗡嗡,身边的人也被我的抓狂搞得万分紧张。并且,工作和生活里完全是两个人:工作是极端的A(严肃挑剔的控制狂),生活是极端的B(和平松弛的大条,常干譬如剪掉火车票记错演出时间白跑一趟的事)。
难道AB型天生这样人格分裂的?我悲观宿命地想道。
男人婆身材壮硕,四五十岁,黑套装短头发,面目粗犷,在瑞典出了名的难搞。J同事不能相信她是女人,直到一起午饭聊天,听她说起讨厌出差,只想回家和两个女儿在一起,业余时间喜欢搞园艺侍弄花草。偃旗息鼓后,发现传说中她的坏名声不过因为她是鲜有的女人做到高层,和传统研发的男性世界分庭抗礼不让须眉,被有色眼镜遮盖掉的缘故。
我本来是这么一个心软的人,却不过因为听信了别人的话先把她置于我心中的死地,抱着一份捍卫本地利益的愚忠大打出手。竟然为了取胜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谋划。真是何苦来哉,不知道图什么。感冒于是拖了一个星期还没好,天天头疼欲裂,杀死不知几多脑细胞。有一刻,我们都觉得凄凉。战火纷飞,回头一看,在这个荒漠的体制里,我们这样努力着变成牺牲品。真是胜有何欢,愈觉得没意思。惺惺相惜倒有一点。
所以,当然要反战!
并且我要向懒散放松不当回事的B型们靠拢,接受感染,走向和平,让大条来得更猛烈些吧!
——写于和热爱生活串胡同听秦腔春赏元大都海棠花六年没见的B型中学同学饱餐一顿之后。
黄昏时分,本地业务大佬特地走到老板和我座位前,说男人婆赞叹,巴巴拉很棒,虽然很tough。我生气地想,你才tough呢,你们全家都tough。
我怎么被血淋淋的工作逼成了这么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挑衅者。想当初面试的时候老被猎头质问,哎,你这么不aggressive怎么能有竞争性呀,跟了老板又说,哎你这么不proactive需要加把劲了。千锤百炼得我变成这样一个咄咄逼人的怪兽。
美女同事在班车教育我一路,说我工作状态过于紧张,弦绷得嗡嗡嗡,身边的人也被我的抓狂搞得万分紧张。并且,工作和生活里完全是两个人:工作是极端的A(严肃挑剔的控制狂),生活是极端的B(和平松弛的大条,常干譬如剪掉火车票记错演出时间白跑一趟的事)。
难道AB型天生这样人格分裂的?我悲观宿命地想道。
男人婆身材壮硕,四五十岁,黑套装短头发,面目粗犷,在瑞典出了名的难搞。J同事不能相信她是女人,直到一起午饭聊天,听她说起讨厌出差,只想回家和两个女儿在一起,业余时间喜欢搞园艺侍弄花草。偃旗息鼓后,发现传说中她的坏名声不过因为她是鲜有的女人做到高层,和传统研发的男性世界分庭抗礼不让须眉,被有色眼镜遮盖掉的缘故。
我本来是这么一个心软的人,却不过因为听信了别人的话先把她置于我心中的死地,抱着一份捍卫本地利益的愚忠大打出手。竟然为了取胜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谋划。真是何苦来哉,不知道图什么。感冒于是拖了一个星期还没好,天天头疼欲裂,杀死不知几多脑细胞。有一刻,我们都觉得凄凉。战火纷飞,回头一看,在这个荒漠的体制里,我们这样努力着变成牺牲品。真是胜有何欢,愈觉得没意思。惺惺相惜倒有一点。
所以,当然要反战!
并且我要向懒散放松不当回事的B型们靠拢,接受感染,走向和平,让大条来得更猛烈些吧!
——写于和热爱生活串胡同听秦腔春赏元大都海棠花六年没见的B型中学同学饱餐一顿之后。
22:48:10 -
bar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