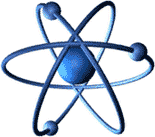Jump to navigation
Barb的不老歌
28 April
兵临城下
虽然没到五一,心情早跟着跑了——在班车上已经困得睡着了,回到家还是不怕,想看碟,因为知道后面有个长假等着,尽可以睡。看Enemy at the Gate不是因为最近迷上了Jude Law,而是因为最实际的原因——好象有马塞克,赶紧看了有问题可尽快拿去换,迟了就卖光了。
不知为何好多人不喜欢这里头的Jude Law,我倒觉得挺好。花絮访谈中Law蓬头垢面的样子,似乎刚丛战争场景里被拉出来,没洗脸,不英俊,比较像个人了——以前像希腊神话。为何有些片子他同同性扯上关系?导演看到了水仙花是也。
[Read More!]
25 April
生命比死还要长
1.
下午看了半个Ripleys Game,很有一点小感慨。
先开头慢慢悠悠的,看的还不怎么着紧,可是有两个片段真动人心魄,一是得血癌的邻居乔纳森在昆虫馆杀俄罗斯人的时候,镜头狠狠地拍螳螂打架,让你提心吊胆等着老头儿被谋杀——当然是为初为杀手的乔纳森担心。那种明知道一个结局,却在紧张的铺垫中等的滋味令人难忘。当然,乔纳森完美地完成了谋杀,消音器质量好得出奇,直到俄罗斯人的血溅满了玻璃,整个昆虫馆里还是悄无声息。
另一个是Ripley和乔纳森在火车厕所里杀俄罗斯人的三个同党时,彪悍的三个黑社会一个接一个晃过来自投罗网——可是半吊子杀手乔纳森显得那么不专业,我们只好为Ripley捏一把汗……导演竟然是个女的,厉害,让人活生生感觉到那种tension.
刚开头看不出来什么,看到后来,往前一想,觉得真好看。
偶觉得马尔科维奇的眼睛和别人大不一样,比如Jude Law吧,眼睛是往外放光的,整个儿像玻璃,让人想起彩云易散琉璃脆之类,可马尔科维奇的眼睛是往里吸光,像黑洞。任何东西进入他的视线,立即化为乌有,可你明明知道,那双眼睛洞察这世界一切罪恶与秘密。
[Read More!]
24 April
他乡的温柔梦境
看《军官与男孩》,久久不愿醒来,像飘荡在他乡的一个温柔梦境,又像随着某首老歌,浮沉于浪尖之上,“……是这般柔情的你,给我一个梦想,徜徉在起伏的波浪中盈盈地荡漾,在你的臂弯;是这般深情的你,摇晃我的梦想,缠绵象海里每一个无名的浪花,在你的身上……”虽然,这嗅得到海洋蓝色的爱情,是回响在两个男孩的身上。
[Read More!]
18 April
云门的X个瞬间
1.怀人
2.辽远的忠孝节义
3. 就这样舞蹈变成我生命的全部
4.时辰到,弃朝廷,望家乡,去路遥(夜奔)
5.轻轻一跳,飞入巴黎的夜空(Nijinsky)
6.十年的生长,十年的学习,十年的演出,以及三十年的销蚀(Nijinsky)
7.佛朗明哥的卡门
8.旷世巨星(Nureyev)
9.追访有情人
10.Like Electricity(Billy Elliot & Adam Cooper)
-- ---------------------------------------------------------------------------------
1.怀人
半月前接到一位朋友的短信,说,上第欧根尼看看。第欧根尼是我一直去的小坛子,可是因为忙乱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已经有大半年没去了。我遵嘱上去,看到一个贴子,标题是《怀人》,点进去只有一张图,我看得懂那是一套碟的封面,上面一行行标题写着:行草、家族合唱、白蛇传、我的乡愁?我的歌、九歌、薪传、流浪者之歌、竹梦、水月——这已经足够令我热血沸腾了。
四年前,我写了一篇关于云门舞集2的文章,那是我第一次宣诸语言,来描述看过现场舞蹈后的感动,从此我自己成了云门的忠实信徒。可惜除了那次云门2到大学的免费演出,以及曹诚渊(曾是香港城市现代舞团的艺术总监)对于现代舞历史的演讲,再没什么机会近身看到那些激烈而优美的舞蹈。所以,林怀民的《云门舞集与我》一出版,我就疯魔一般四处搜罗,终于在上海买到,了了一桩心事。
一九七三年,林怀民二十六岁,云门舞集成立伊始。最开始令我不置信的是,他本身是学新闻的,又一直写小说,只因观舞时那种感动与热忱,放弃一切投身舞蹈。即使到今日,舞蹈,尤其是现代舞,仍是小众的艺术,未必得到许多认同。但他及云门一直起着开山铺路的作用,把现代舞推出去,让更多人领略这种美。看了《云门舞集与我》,了解幕后那许多艰难及辛酸,包括我在内的观者应觉得有福了,而林怀民一支热诚又极端优美的笔,又让我摈弃外在的红尘滚滚,一头沉浸在那个“人的肢体从不扯谎”的世界。
2.辽远的忠孝节义
林怀民写到某次在街头看草台班的歌仔戏,即便唱戏的跳出戏里与胡琴手吵架,观众也能或蹲或站在台下看得津津有味。“台下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戏,前世故人望忧的你可曾记得起”,他们皆知那是戏,然而只要片刻就可以投进了戏里,忘记身边的艰难苦恼。
这样的草台班让我想起《新不了情》里,阿敏的妈妈、舅舅及阿玲。阿敏那样有天才,难得的是窝在任何一个角落里,再怎么流离,都用那份乐观感染人;阿敏的舅舅,老、病,可是偶尔一曲In the Mood,让自诩专业的阿杰感动了,Jazz是要这样,即兴的、深藏的激情,技巧只是为了烘托这些;阿玲,草台班的台柱,小气贪便宜,但是当你看到她放低尊严处处与人计较,换得的是深藏箱底的一套水钻、戏服——那明明是深藏心底的一个梦,你还要小看她么?阿敏的妈妈,年轻时曾经很美丽,才华横溢,老了,岁月只在她的脸上、腰身留下痕迹,她不声不响地默默退于幕后,经营戏班子,掌管生活起居,可是女儿病了,她便又换上晶晶亮的歌衫,唱:“往后的岁月,苦痛要做人,欢笑也做人……人生难免有爱、有恨、有喜、有悲、有聚、有分、有笑、有泪,愿你永相陪……”
云门刚开始的艰难或许不下于草台班,所有的舞者却用尽心力挥尽汗水排练——她们当然不是最好的,最好的那些舞蹈天才们或许都在大剧院里演绎着经典芭蕾,可是她们都像林怀民一样,是被心中的一股热驱动,就这样投入自己的一切,身体力行。我曾经抚摩校园的日晷上,“行胜于言”四个字,这四个字在她们身上贯彻得最彻底,所以遇到极美的舞蹈,我们只能付出一遍又一遍的掌声,言语是无力的。
台北草台班,“对白里夹杂着耳熟的流行歌,徐徐缓缓演出的却是辽远的忠孝节义”。云门自己也把积攒了千余岁月的那些京剧故事搬演到现代舞的舞台上来。他邀了吴兴国这个大孩子,把复兴剧校的训练带去云门,把《乌盆记》改编成《奇冤报》——如果你看过吴兴国写的《自我学戏的那一天起》,便会知道,这个《奇冤报》中可爱的鬼,也有多么决然的坚持。吴的文章中的刚毅和敏感,和林怀民如出一辙,更一致的是,他们文字里那种奇特的韵律之美,无须雕文造句,完全来自他们各自人生路上所坚持和追求的。
一样的坚持与敏锐,使得舞者吴秀莲“在《乌龙院》中,她的阎惜娇就是这样尖锐地把宋江逼得无路可走”。
“舞者的生涯是寂寞的。肢体是他的世界,惰性是他的敌人。流汗喘息,朝夕苦练,但求灵活舞动,作完美的表达。偶尔荒废功课则前功尽弃,从头再来。舞者不是机器,机械式的规律却是一种必要。台上的几分钟,往往是多年苦练加上数次排演的结果。然而,掌声不是最终目的,舞者最大的满足在于自我完成。”
从《薪传》到《秋思》,到《九歌》到《水月》,云门就是这样继续着传承。——我常想,京戏昆曲粤剧豫剧歌仔戏……但愿那些美丽的传奇永不湮灭,再让云门这样年轻的团体,不停演绎自黄帝以来,传说中的乐舞吧。
3.就这样舞蹈变成我生命的全部
现代舞的拓荒者,创造“缩腹-延伸”技术的玛莎葛兰姆有句话说:“我没选择成为舞者。是舞蹈选择了我,就这样舞蹈变成我生命的全部。”——林怀民教课,舞者认真练习,下课后舞者们习惯性地趴在地板上喘息,林怀民离去时,她们坐起,静静地说,老师,谢谢你。林怀民冲下楼,在无人的黑巷里狂奔,流着泪,便是想起了这句话。
一九八零年春,美国公演归来的云门到低收入地区做免费演出。“松山商职操场野台演出是在雨中进行的,观众六千,自始至终不肯散去。”
一九七八年,林怀民编作《薪传》,心里涨满无名焦虑,说,“时代是一片压肩的乌云。”《薪传》以动作为反弹,“嘉义体育馆首演之日,舞者汗泪齐飞,观众含泪鼓掌。”
自这本书里,看得到林怀民不只关注舞台小世界,他看到政治、民生,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却绝不是抱着同情的心理,浪迹四海,反倒时时从草根阶层得到激励,反过来,他敏感锐利的记录,也激励任何一个读者。一位爱《易经》的出租车司机说:“《易经》学会不让我参加,因为少年贫赤,只有小学学历,干你娘,我就写一篇论文给伊看。不让我入会也给我进去了。”
台风登陆的午夜,林怀民醉酒叫车,适时正满心抗拒云门欧洲之旅,因为不愿再面对舞者抛家弃子,每日一城咬牙演出的痛苦。那日他和一位瘦削的黑衫青年风雨同乘,原来他是建筑工人,退伍一年多,收入微薄,如果加班尚能添些少外快,有问必答,很安静,也很简单。林问他,辛苦吗?他诧异地扭过头来:“什么工作不辛苦?”
第二天,林怀民“改邪归正”。
4.时辰到,弃朝廷,望家乡,去路遥
林怀民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欣赏者,他不止用自己的身体去演绎,更用极其细致的领悟力描述所触及的一切艺术的美。人生多次最美的相遇便在于此,不经心的,并未众里寻她,不必蓦然回首,只在你经过路上,一瞥或没有,遇不遇在一转念。如果没有林怀民这本书,便未必有机会想到下面的情致。
七四年春,林怀民前去日本,追寻中国古舞,到明治神宫附近聆赏雅乐。“
路灯下走过迂回如河川的小巷,推开一扇木门,时光突然静止。模糊的琵琶、笛声,浮在晚春的夜晚里。踩过地下的樱花,沿着苔青的石板道往前走,黑暗的深处流泉淙淙,忽然想起李义山的诗:‘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
雅乐现场,“越天乐”长极无聊,倒让林怀民松弛身体,然后,急音促拍中“兰陵王”登场。“曳长裾,持金桴,戴着一个龙首似的面具——兰陵王俊美英武,戴面具迎敌。 ”并未着力,只是“ 缓步、低蹲、跺脚”,“ 徐徐缓缓舞出的是兰陵王的雍容大度,是‘气’。”(郭富城有一段舞“狂野之城”,就是仿雅乐的,把这几步动作做得充满了力,背道而驰,仍然很美。林老师若知我拿郭富城比雅乐,8知会8会生气)
求舞的过程教林怀民觉得屈辱与悲哀——要远去和日本人学习中国的古舞。幸而老师狠狠敲打之余倾心相授——又是一种传承,这种“传”,有它的诚意在,这是艺术跨越民族国界之处了。
记得有一次看李碧华写在香港看林怀民的旧作《红楼梦》,标题是《万艳同杯借梦尝》。借她的眼中看去,“ 林的《红楼梦》不讲故事,放弃表情,忘记名字。”只是金黄、紫、白、绿、粉蓝、橙、秋香……各色的衣裳,我但愿能想象那“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深院内旧梦复浮沉……”
林怀民和李碧华是一般钟爱传统戏曲之人。林怀民提及《思凡》里尼姑带发修行,满头珠翠,梅兰芳解释,这是为了观众视觉的美感。“
再恐怖的故事莫不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演出,昆曲戏剧‘无舞不歌,无歌不舞’。 ”
我记得有次偶尔一开电视机,看到裴艳玲演的《夜奔》,眼睛就瞬也不瞬地跟下去,连呼吸都静止——林冲唱“数尽更筹,听残玉漏”,双手平伸,左右双弧,象征所挂玉漏,“逃秦寇”,转身向门外高指,“哎,好叫俺有国难投”,双手击胸,踢腿,半转身疾走圆场,右手按剑左掌扬出,“哪答儿相求救”,接着,“欲送登高千里日,愁云低锁衡阳路,鱼书不至雁无凭,今番作悲秋赋。”——好男儿有国难投,这是一个人的舞蹈,林冲那股悲怆之气令我胸中顿生臆闷,从此反复想起英雄末路那几句——“时辰到,弃朝廷,望家乡,去路遥”。林怀民亦说,林冲的挣扎,“
比起许多人津津乐道的现代人的孤独感,不知深沉多少倍。”
林怀民又说马友友,“坐在倒数第三排,一样可以感染到那么自信而豪迈的生命力。”他的描述真好,让我感同身受。而他的描述最珍贵的,是自雅乐想到德彪西,又从德彪西想到“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艺术之美到了极高境界,原应是相通的。
5.轻轻一跳,飞入巴黎的夜空
《云门舞集与我》分上下两编,上编,是林怀民与云门一路走来的欢欣泪水,下编,是简单介绍现代舞的历史,从垂死的天鹅到玛莎葛兰姆,以及那短短历史中几颗闪耀最明亮光芒的星星。
虽然短,可是这是一段极美的艺术史。从《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到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我对艺术的认识极无章法,碰到一点儿,学一点儿,享受一点儿,放弃一点儿,这种无章法让我自己的摸索很容易变成徒劳,可是太深的积累需要时间和精力,是我在现阶段无法付出的。但由这样精彩的人做这样简单深辟的演绎,令我的所知与享受都事半功倍。
《天鹅湖》是西洋舞蹈的分水岭,在那之前,是十五世纪路易十四的“梨园”。一八三零到七零年,“浪漫芭蕾”缺乏新意走向衰落。一七三五年,俄国的安娜女皇成立了自己的皇家舞校。一八四七年,法国舞者倍第巴(Petipa)应邀表演,却一待六十多年。他拒学俄语,以法文教学,自此,法文的芭蕾术语全球通行。
一八七七年,倍第巴与柴可夫斯基合作,编出《天鹅湖》;一八九零《睡美人》;一八九二《胡桃夹子》。芭蕾展开璀璨的年代,却一直以女舞者为重。
其后代有才人,狄亚基列夫(俄国芭蕾舞团创办人)、舞蹈史上最感人的传奇尼金斯基、乔治?巴兰钦(俄国芭蕾舞团时期,他的杰作是《阿波罗》与《浪子回家》,“新古典”芭蕾的滥觞)、安娜?芭芙洛娃《垂死的天鹅》感召一代人。一九四九,《睡美人》公演,玛歌芳婷一夜成名。在佛罗伦萨,邓肯盯着波提切利(师太的鲍蒂昔里)的《春》,直到“百花为我齐放,女神开始摆动身体”。她自己台风惊人,“
静止不动便压住全场。忽而,她举起一只手仿佛揭示了奇迹。 ”
圣丹尼斯与丈夫铁雄扮神,搬演异国情调。葛兰姆(《悲恸》、《原始的神秘》、《新境》)与韩福瑞(《水舞》、《震荡教徒》、《帕莎卡里亚与赋格》)为现代舞拓荒。
这些人不是悬挂天幕的星星,林怀民的描述为他们增了血肉,活生生地呈现在你我面前。
一九零九年,狄亚基列夫带去的俄国芭蕾使世纪初的巴黎举城若狂。最让巴黎人倾倒的是狄亚基列夫的同性爱人,首席舞星尼金斯基。他的身体粗壮,土气十足,腼腆、敏感、寡言,平时排演也不出色,可是一上台,即绽放星辰亦难以匹敌的光芒。“
在《玫瑰花魂》的结尾,尼金斯基轻轻一跳,‘飞入巴黎的夜空’。”
尼金斯基生前毁誉参半,一时用力与美征服观众,一时又在《牧神的午后》做自慰的动作,引来卫道士的一片嘘声。《春之祭礼》是史特拉汶斯基力作,“
《火鸟》、《彼楚虚卡》中甜美的俄国旋律付诸阙如,惊天动地,强有力的节奏,有如大地的脉动贯穿了全曲。七十年后的今天听来,依然觉得新鲜震撼。”《春之祭礼》也是尼金斯基的呕心之作,他充满新意的创作狂舞却引来不同欣赏口味观众的斗殴。他自己生命的春天却已近尾声。
因为和同一舞团的演员恋爱,旋即结婚,尼金斯基引来狄亚基列夫的震怒和弃绝,从此走上漂泊的命运。一九一九年,在瑞士作最后一场演出后,他精神崩溃,被送入精神病院。
6.十年的生长,十年的学习,十年的演出,以及三十年的销蚀
“ 十年的生长,十年的学习,十年的演出,以及三十年的销蚀。”一位传记家如此总结尼金斯基的一生。林怀民说,他的重要性“不在于集天才与疯子与一身的传奇,他辉煌的表演提升了男性舞者在舞蹈界的地位,人们爱用‘尼金斯基再世’来形容优秀的男性舞星。”
我自己一向是个腼腆的人,很少做任何事吸引众人的眼光,我自己记得的唯一一次,是在听曹诚渊演讲时,因为有事提前离席,飞快地写了一张纸条,噔噔噔噔,从最后排的座位跑到前面,伸长手臂,递到曹诚渊的手里。现在还记得清楚,那张纸条,一是感谢他精彩的讲述,二是问他引起诸多争议的全男班“同性恋”《天鹅湖》——芭蕾终于打破了那个女舞者时代的禁锢,我记得很清楚,即便是照片上,那张全男班天鹅湖照片中也透得出舞者身上腾腾勃发的男性力量。
一九八七,失传四十七年的《春之祭礼》通过杰弗雷芭蕾舞团年轻舞者的身体在洛杉矶音乐中心重现人间。尼金斯基辞世三十九年后,林怀民去看了《春之祭礼》,说,的确,像当年巴黎舞评家说的,那是一场“从显微镜看到的”“ 爆裂、缤纷的飨宴”。
舞蹈最令人激动人心和恋恋不舍的就是这一样——一切只在瞬间,在你眼前爆发最绚丽夺目钻石一样的光芒,让你片刻间双泪长流,又在瞬间熄灭,起立,鼓掌,落幕,熄灯,光之陨落毫无声息,像人世间的恋爱,一切会随时间流去,无从记忆,只有最初那一刻受到的震撼长留心底。
对于更多舞者也一样,即便像尼金斯基一样,十年的生长,十年的学习,十年的演出,却未必放出那样耀眼的光,就像那位在芭蕾舞界独霸天下的狄亚基列夫一样,“所有的努力只证明才华的不足”,多么的伤感,也只能走向销蚀。
舞蹈是这样考校天分而且残酷的艺术,像《垂死的天鹅》,那是“
一支考验舞者艺术素养的独舞,讨好,却难跳好。比较去年‘明星舞团’蔻克兰与‘阿庞德舞团’莎金的演出,优劣高下,在出场半分钟内立见分晓。 ”
7.佛朗明哥的卡门
昨天我买了一张佛朗明哥卡门的碟。
碟店里人声浮动,我让店主放一下卡门,先看到大剧院座无虚席,下一段卡门已经在舞着裙子唱了,花絮里,有一段舞者的排演做了特效处理,感觉那大红裙裾和着伴舞黑色的手臂在拨弄着音乐,激烈欢快的西班牙气息。这舞蹈足以将我带离此地。
半个月前,接到一个6位号码的电话,我很诧异,以为必然是做电信工程的朋友在试机,电话那边有点嘈杂,听不太清,我扯着嗓子“喂”“喂”两声,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远远唤我:“Barbara——”我很激动,问:“Tim,怎么是你,你在哪儿?”
Tim是我的前老板,五十几的老头,资格比我老得多的影迷,工作上是我的导师。因为电影结缘,一老一少,常常跑去吃小饭馆买D版碟。我会看他推荐的Mephisto看得睡着,他也会死命贬低我推荐的《情书》,我诧异他为何喜爱《刀马旦》,他纳闷我怎么爱看伍迪艾伦,有时互相赠送影碟,又或是一起抢夺碟店里最后一张《无主之地》。他是土生土长的纽约客,婴儿潮时出生,曾经狠狠地叛逆过,在法国左岸小酒馆流连,又或是在马德里街头参加奔牛。看过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非常像《十二怒汉》时的亨利?方达,平时爱穿夹克戴鸭舌帽,我老公常笑他假扮罗伯特德尼罗。那真是一段快活的日子。
后来他该回去了,前一晚,留mail给我:感谢你,这个special firend。回去前,他太太来北京接他帮他打行李,她是中国人,前北京体操队队员,十年前与他相识结婚,相濡以沫。他们的行程是,先去夏威夷——那是他念念不忘的天堂,再返纽约。就在夏威夷,拍照时她失足落水卷入旋涡,不治而逝。
此后的email里我不太提此事,然而他总用她奋斗的例子教我如何应付工作上的危机。他曾提过,从夏威夷返家,看到家里处处是她留的卡片纸条,然而斯人已去。他无子女,美国人的晚境似乎本来就颇凄凉。
这次电话里,因为纽约太远,远得像真空,我放下平日里的一切小心,脱口问了不该问的话,我说,Tim,are you happy?
沉默半晌,他说,No, Barbara. How can I be happy?
——以前,我记得他一直非常欢快地在寻找佛朗明哥的卡门,想给我看,自己几乎都哼出歌来,却迟迟难觅。这下,看到这张卡门,他该高兴点了吧?
听到卡门序曲,想起那段不知是谁填的中文词,“什么叫情,什么叫意,还不是大家自已骗自己;什么叫痴,什么叫迷,简直是男的女的在做戏;你要是爱上了我,你就自已找晦气;我要是爱上了你,你就死在我手里。”
这段词出现在李碧华的《胭脂扣》里,趁着如花无从兑现的寻人启事:十二少,老地方等你,如花。无处着力无从下手的悲凉。
罗文唱过这歌,黄宝欣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里也唱过。唱得狠狠的,似乎洒脱,却更像感叹。
这尘世间的故事啊。兴许是我错了。卡门是个悲剧,她的热情不过是为了追寻。
这些是题外话,皆因林怀民这句而来:“我不知舞蹈可以如此有力,如此动人。如果穷尽一生可以通过动作说出几句清楚的话,余愿足矣。”电影是语言,音乐是语言,绘画是语言,舞蹈更是,然而人世间总有一些情怀,任何语言难以描述,自此,是怅怅地去了。
8.旷世巨星
“旷世巨星”并非舞评家的封赐,而是我心里赠予纽瑞耶夫(Rudolf Nureyev)的名字。我不知道除了他还有谁当得起这样一个横扫天下的称号。
我很记得那个炎热的夏天下午,我正在家里随意地呆着,走动,抹碟子,空气又热又闷,我擦着额头的汗随手按下电视遥控,中央6台正在放一套黑白记录片,一个年轻的男子,跳着芭蕾舞。那片子很长,怎么也不完,我却被那男子身上的熠熠光芒吸引,看着他排练、公演、叛逃、迎接公众的欢呼与掌声,呼吸渐渐地紧了。就是这样,我如此漫不经心地让纽瑞耶夫这个名字走入我的视线。
“《吉赛儿》第一幕。布景是远山茅舍。弄人打扮的演员跳了一段乡村风味的群舞。村故吉塞儿出场,轻巧地独舞之后,加入群舞。众人在转了又转,转了又转的高潮中摆出一个漂亮的画面,退场。急促的音乐带出男主角阿尔布雷特——飘着黑色大斗篷,踩着风般的步子,驰至舞台中央,煞步,亮相。观众疯狂了。掌声持续两分半钟,乐队指挥不得不放下指挥棒。”
“ 这一切只因为扮演阿尔布雷特的男士名叫鲁道夫?纽瑞耶夫。”没见过他表演的人,在形容优美的动作时,也会脱口而出:“那是非常纽瑞耶夫的。”
纽瑞耶夫,曾经叫Rudik,鞑靼人的后裔,出生在前往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他认为这注定了他一生要动荡不安,要跳舞。一位芭蕾舞者说过:“纽瑞耶夫出生在火车上,往后他也以时速100哩的速度度过了一生。”可是学舞的愿望直到他十七岁才得以实现。他用决心与努力在三年内通过列宁格勒芭蕾学校的严格课程,进入一流的基洛夫舞团,但表演的机会少得可怜。他只是个新人,叛逆的个性又为他四处树敌,舞团首脑对他防卫森严。
一九六一年,纽瑞耶夫随舞团往巴黎演出。在巴黎,他放浪形骸,交友游荡。在飞机飞往伦敦时,他逃脱了秘密警察的追逐,叛逃法国,受到政治庇护。这时他是Rudi,变成国际性的性爱象征,他的狂放不羁进入了颠峰。
他参加嬉皮聚会,与同伴被捕入狱。在高级晚宴中拒吃自助餐,把盘子摔到墙上,宣称“纽瑞耶夫是被人伺候的。”在意大利表演时,舞伴不小心踩落他的鞋,纽瑞耶夫当众赏她一记耳光。
这是个坏脾气的,被惯坏的孩子。他是欧美芭蕾舞台上叱咤一时的暴君,又有人说他是“ 一位顽童、顽劣份子、卖弄风骚的性感大男孩、欲海沉浮的王子”,因他始终率性,忠于自己。
刚刚看了皇家芭蕾舞团的一张碟,纽瑞耶夫与玛歌芳婷,同时照亮二十世纪的两位芭蕾巨星。第一段是天鹅湖,纽瑞耶夫出场短短数次,每次都抢尽我的视线,他甘心托举她们,甘心隐身其后,因为他一举手一投足就是挡也挡不住的光彩,他甚至不必大动干戈,只是站在那优美的曲子里,轻轻舒缓手臂,就已经胜过千言万语,胜过玛歌芳汀无数炫技的动作。纽瑞耶夫一身白衣随意而立,已让人一生无法忘记。
第二段是海盗,无法想象,非常瘦的纽瑞耶夫能爆发出那么猛烈惊人的力量,他随意托举着她,做腾空的动作,像是这世界都撑在他手里,却又毋须担心,只需交付信任。
书中有张最美的照片,那是纽瑞耶夫和玛歌芳婷舞台上的特写,她依在他的怀里,他略微侧着头,光和影清晰地勾勒出那俊美的容颜。另有一张《吉赛儿》的剧照,他无限忧愁地靠在玛歌芳婷怀中,可以看得出,玛歌已经老了,他却是全盛的时候,宛如田野里最繁茂的百合。
这个时期,才是真正Rudolf的时期。在维也纳的一场表演,“掌声使他出来谢幕八十九次,历时一个半小时。”
一九九三年,纽瑞耶夫结束了与艾滋病12年的对抗,在荣耀中骄傲地逝去。他现身这世上,似乎只为给人留下一个美的传奇。有人评论他说:“他的飞身旋转与跳跃每每令观众目眩神迷,那惊人的爆发力与热情无人能望其项背。他的一生仿佛快速闪映的幻灯片,紧凑、精彩、毫不留白。舞台上舞台下的纽瑞耶夫,都是一个惊叹号!”
在看罗伯特雷德福的电影《大河恋》时,看到布拉德皮特,碎金发在田野溪间闪耀,他的眼睛里带着光,钓杆远远甩出去,他带着青春无匹放肆不羁的笑容,我仿佛看到纽瑞耶夫的倒影。然而纽瑞耶夫是不世出的,布拉德皮特那样美丽的形象灵光一现,带着雷德福对自己的青春的缅怀,成为一记绝响。
到了今天,《魔戒III》横空出世,Legolas迷倒全世界的fans,我后知后觉地看着那个精灵,后知后觉地看蓝莲花编排Orlando和Viggo的《只是当时》,迷迷糊糊地想,怎么,这个孩子让我觉得有点熟悉。今天重新看纽瑞耶夫深藏在身体里的激情,我又想起了他。是呀,如果《只是当时》成为真的,那纽瑞耶夫便是悬挂在天边的一面的镜子,深深映出,这个世界里所有的美、放浪的追求和最深切的痛楚。
9.追访有情人
《追访有情人》是个不咸不淡的故事,可以不那么用心地去看。韩国片子闷的闷死,闹的闹死,这个故事基本属于前者,但是淡淡流韵,可以在心静的下午,一边手中做着事,看下去。男主角(李成宰)是纪录片导演,他惯于用摄象机记录世俗的真爱,有时这摄象机放出的朴素片段甚至聚合一段濒临破碎边缘的爱情。他拍到一个特别的女孩子李永喜(沈银河),她对着镜头,说自己是发型师,男友正在服兵役,说琐事以及思念——这一切都是谎言,她说着别人的故事,来掩饰自己的心碎。他想跳出摄影机,探索她的真相,却被带到她爱人的坟前。
——这些与云门不相干,唯一相干的,是舞蹈,电影里看似与剧情无关的舞,沈银河穿着一身大红的衣服,和男舞起舞的片段在电影间隙中倾泻而下——衣服是红色的,热情如火,身体却写满了悲怆。“人的肢体从不扯谎”。
10.Like Electricity
我看了两遍《比利?艾略特》(《跳出我天地》),还愿意继续看下去。看迷人的英格兰,小镇海天相接,罢工的阴鸷,日常生活的辛酸与这辛酸中温暖的亲情,以及比利心里那一点点梦想的火。
不仅仅是梦想的火。还有一个人的天赋际遇,比利的老师、拳击教练、父亲、哥哥、奶奶都是让人难忘的,可我更记得他幼年的朋友麦克——比利喜欢跳舞,麦克喜欢穿女孩子的衣服,比利进了伦敦的舞校,麦克远远地相送。比利舞台公演,比利的父亲发现身边坐着一个古怪的女装男人,还冲他打招呼,大儿子告诉他,那是麦克。
命运把人推向殊途,如果有一点点差错,不是终结,便是辗转与曲折。比利实实在在好运,从小镇跳到了大舞台。然而比利的成功或许也只是群舞,天鹅中的一只。名气只垂青不世出的天才,更多人成为陪衬,然而他们还是在跳,如同比利一样,为的是自己身体的呼唤。云门没有独舞,更多的是群像,从《水月》到《薪传》,挥汗如雨可能只是在成就编舞者的理想,可是还是在跳。
《比利?艾略特》的最后,父亲背叛罢工,赚得微薄的工资,带比利去伦敦考芭蕾舞校。面试时小比利正和人打架打得落花流水,眼看是没希望了,考官叫返他,问:你跳舞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比利发怔,犹豫,说:我也不知道。慢慢想了想,说:“我不知道……感觉很好,开始有点僵硬,但是只要一开始跳,我就会忘记一切……好象自己不存在……我感觉身体的变化,好象里面有一把火……我自己像小鸟……like a bird,like electricity. Yes,like electricity.”那一瞬好象也有一股电流穿透我的身上。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你是意义,是天是地是神的旨意……”——看,人对于所爱的描述,大体相同。
我最爱片子结尾那一幕,成年后,学成的比利出场——从那半裸的背影我们几乎认不出他,肌肉纠结,他那么高大、优美的身躯,身体的倒V形,纠结着青春健硕的肌肉,他的脸上有妆,身上饰着天鹅的羽毛,没有丝毫小比利的痕迹,只是充满了华丽的美与力量,高高的飞跃,跃破了时空,跃过梦想的界限(我猜,这便是我想看的那一幕,全男班的天鹅湖——刚发现,那副身躯,是Adam Cooper)。
林怀民在书中说,八十一岁的玛莎葛兰姆仍然带着舞团公演,当她现身纽约,全场观众起历喝彩,她静立答礼,“二十世纪的神不经诰封,而是服从意志,执著奋斗的自我完成。”
10 April
“这儿总算有一位真正的恋人了!”
几次三番,我差点与Wilde失之交臂。第一闪念,因为那个片名《心太羁》。这类不明所以的名字也不知是谁取的——要说有票房效应倒真未必,就像84 Charing Cross Road,生生变成了碟壳上的《迷阵血影》,既害了我这样想看的人,更害了因为片名买回去看的人。
第二闪念,是看到Stephen Fry,这是谁?不认识!这时碟店老板适时地跳出来(像以前每次热心向我兜售他心目中好碟的瞬间),向我指出:“收了它!”第三闪念,我正在balance老板以往的坏品味(想想看,他宁愿坐拥一大堆我求之不得的D9,花29刀买原版的Dave,我只好说他是个爱浪漫的人)和一如既往对电影的热诚时,看到Jude Law,天,这个好莱坞油脂!为那天买碟超出预算,我简直是在万分挣扎中放弃《大鼻子情圣》,拿起Wilde。
等到听从师父(俺的师父是Jun)的吩咐看完了,才想起《喜宝》里,成为“约翰兄弟”的家明反复强调的那句圣谕,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
[Read More!]
06 April
他和他和他和她
我和《美少年之恋》没缘分,因为历尽了周折。
要从初识杨凡这个名字开始。
[Read More!]